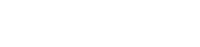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55章 一个错步便能封喉断脉
“贵客临门,祥云绕樑。”
院外忽地传来三声叩门,沉稳而篤定。
顾天白心头一怔,想不出谁会寻到这偏僻小院来——歷下城中他举目无亲,若说是房东,租金早付足两月有余,断不至於此时登门催扰。
他霍然起身,步至院门,手按门栓,並未急启,只扬声问:“何人?”
门外寂然无声。
他纹丝不动,指节微扣木栓,脊背绷紧如弓,静候片刻。须臾,叩门声再起,依旧无人应答。
顾天白眉峰一压,双臂筋络骤然绷起,腰胯沉坠如山桩,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隨时准备旋身护住屋內姐姐——三年流徙,昼伏夜行,仇家追索如影隨形,早已把警醒刻进了骨头里。
门开一线,紫袍猎猎映入眼帘,是张九天;他右肩侧立著素兰道袍的张九清;再往后,韩鯤鹏与韩有鱼並肩而立,神色沉静。
“顾天……”张九天刚拱手开口,院內猛然炸出一声怒吼——
“狗贼!拿命来!”
却是薄近侯一路尾隨顾天白蹭到门前,原只瞥见两个道士,其中那女冠还是昨日照过面的,待目光扫到韩有鱼脸上,霎时血涌上头,恨意翻江倒海。
这一嗓子劈得张九天话音戛断,也惊得顾天白肩头一震。
这几日薄近侯满心只缠著报仇二字,钻了死胡同,哪怕拳脚未精、气力未纯,也要豁命扑上。
风声撕裂空气,宣花斧拖地而行,颳得青砖迸火星子;
三丈距离被他三步踏碎,长斧已抡至半空,寒光劈落,直取韩有鱼天灵!
顾天白未回头,却已听清破风之势——韩家兄弟不足为虑,可张九天、张九清近在咫尺,一个错步便能封喉断脉。
他眼角余光扫见张九天左足微旋,不丁不八,拂尘梢尖悄然离臂,蓄势待发。
电光石火间,他斜身滑步,让开锋刃,顺势后撤半步,撞进薄近侯胸前破绽,借力一送,力道巧如抽丝。
薄近侯热血冲顶,脚下虚浮,被这一撞踉蹌倒退,噔噔噔连退三步,身子还没站稳,忽觉手腕一沉——顾天白已侧身探手,稳稳托住斧柄,千钧之力被他单臂接下,也剎住了薄近侯溃散的势子。
前后不过眨眼工夫,顾天白已挪步贴至薄近侯身侧,两拨人马就此隔门对峙,一在檐下,一在阶前,相距丈余,气息胶著。
“顾天公子好功夫。”张九天抱拳含笑,略一俯首,礼数周全,挑不出半分疏漏。
顾天白不接话,只將巨斧轻轻搁地,反手扣住薄近侯腕后命门,一股绵劲透入,瞬间卸尽他一身蛮横气力。
昨夜偷听来的只言片语此刻浮上心头——原来他们寻的,正是自己。
终究没藏住,被人循跡找上门来。
他默然垂眸,姐姐却已缓步而出,指尖掸去蓍草茎叶沾的泥星,笑意淡淡:“方才閒坐卜卦,得『利东方』之象,果然紫气盈庭,贵客登堂。”
“顾二小姐安好。”张九天再度躬身。
“尚可。您便是九天道长?”姐姐语气平和,礼数不乱。
张九天抬眼望去,见她清秀面容上双目空茫,当年传闻果真不虚,心底轻嘆一声,只道:“正是贫道。”
姐姐脚步微顿,恰停在薄近侯身前,抬眼望向张九天:“不知道长此来,所为何事?”
名门教养刻在骨子里,举止从容,不卑不亢。
一问一答之间,张九天暂且压下对那持斧少年突袭的疑虑,先作揖答道:“贫道与师妹张九清奉师命游方,途经歷下,听徒孙说起二小姐与三公子在此棲身,特来拜会,叨扰之处,万望见谅。”言罢又是一礼,端方守矩,无可指责。
姐姐唇角微扬,一声轻笑似风掠竹:“佛门弟子,敢打妄语么?这话一出口,便落了邪见——拜不得无上师宝,修不了玄中大道。”
这次张九天却沉默了,只把笑意堆在脸上,静静望著姐姐。
姐姐压根没指望他接话——她这番话里裹著冰碴子,字字带刺,句句含锋,分明是拿话当鞭子抽人。
但凡有点脑子的,谁肯往这刀尖上撞?
她紧接著又道:“依我所知,九天道长与九清道长这对道门璧人,平日不是在紫禁城內开坛讲经,便是在圜丘台上焚香诵咒;
再不济,也该窝在武当藏书楼里翻那些泛黄髮脆的道藏典籍。
哪来的閒工夫,跑到歷下城这种地方溜达?
再说,眼下已入正月,朝廷年后头桩大事就是开朝大典,道长不赶回京城候命,倒有空来这儿虚耗光阴?九天道长別绕弯子了,有话痛快撂出来便是。”
张九天仍只噙著笑,任她说完,也不辩解。张九清却按捺不住,火气直衝脑门,冷喝一声:“小丫头片子,嘴倒是利索!”
姐姐耳朵轻轻一抖,笑著接腔:“哟,九清道长也在啊?果然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形影不离得很。可我跟九天道长说话,您插哪门子嘴?
出嫁从夫的道理都拎不清,三从四德怕是连边儿都没沾过吧?
难不成还得我这未嫁闺女,手把手教您规矩?”
“你……”张九清一时语塞,刚要发作,却被张九天一挥拂尘拦住。
他这才缓步上前,接过话头:“顾二小姐说得极是,是贫道俗气了。实因前几日山中接到徒孙密报,说似见二小姐与三公子现身歷下,拿捏不准真假,这才劳烦我们夫妻走这一趟,只为当面確认。”
“確认完了?”姐姐眼尾微扬,明知故问。
张九天呵呵一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得回山復命,去向张九鼎稟报了?”
他依旧含笑不语。
“再然后,是不是就要把我和弟弟的消息,散到江湖各处去?尤其要让那位你们连提都不敢大声提的人物,第一时间听见风声?”
张九天心头一凛——这姑娘哪只是伶牙俐齿,分明是听风辨位、见影知形,自己才吐半句,她已把后头七八步全踩准了。
此刻站在她面前,竟像被剥了壳的核桃,里外通透,毫赤裸裸。
於是,他还是笑。
“好,隨你们怎么安排,我也拦不住。不过在这之前,小女子想跟道长討个商量。”
张九天略一怔神,拱手道:“顾二小姐请讲。”
“九天道长可晓得,我姐弟二人,与贵派弟子韩有鱼之间,还横著一桩旧帐?”
张九天神色微动,恍然道:“原来如此。贫道此来,正为此事。是门下弟子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小姐,特地带他登门赔罪,万望二小姐宽宥。”
说著,抬手示意自始至终垂首肃立、未曾开口的韩有鱼上前。
可怜韩有鱼,前日被张九清一掌劈得臥床整整两昼夜,刚能下地,又被拖来此处——他万没想到,这对煞星竟就住在离自己不过两条街的地方。
进门还没摸清状况,就被一个膀大腰圆、拎著丈许长斧的少年兜头劈来,险些把魂嚇飞。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喊一声冤。
“九天道长误会了。”姐姐不等韩有鱼迈步,便伸手拦下,“我这人心宽似海,翻篇的事早翻过去了,赔什么礼?
可您这位徒孙,还干了一件更扎眼的勾当,您知道么?”
第455章 一个错步便能封喉断脉
“贵客临门,祥云绕樑。”
院外忽地传来三声叩门,沉稳而篤定。
顾天白心头一怔,想不出谁会寻到这偏僻小院来——歷下城中他举目无亲,若说是房东,租金早付足两月有余,断不至於此时登门催扰。
他霍然起身,步至院门,手按门栓,並未急启,只扬声问:“何人?”
门外寂然无声。
他纹丝不动,指节微扣木栓,脊背绷紧如弓,静候片刻。须臾,叩门声再起,依旧无人应答。
顾天白眉峰一压,双臂筋络骤然绷起,腰胯沉坠如山桩,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隨时准备旋身护住屋內姐姐——三年流徙,昼伏夜行,仇家追索如影隨形,早已把警醒刻进了骨头里。
门开一线,紫袍猎猎映入眼帘,是张九天;他右肩侧立著素兰道袍的张九清;再往后,韩鯤鹏与韩有鱼並肩而立,神色沉静。
“顾天……”张九天刚拱手开口,院內猛然炸出一声怒吼——
“狗贼!拿命来!”
却是薄近侯一路尾隨顾天白蹭到门前,原只瞥见两个道士,其中那女冠还是昨日照过面的,待目光扫到韩有鱼脸上,霎时血涌上头,恨意翻江倒海。
这一嗓子劈得张九天话音戛断,也惊得顾天白肩头一震。
这几日薄近侯满心只缠著报仇二字,钻了死胡同,哪怕拳脚未精、气力未纯,也要豁命扑上。
风声撕裂空气,宣花斧拖地而行,颳得青砖迸火星子;
三丈距离被他三步踏碎,长斧已抡至半空,寒光劈落,直取韩有鱼天灵!
顾天白未回头,却已听清破风之势——韩家兄弟不足为虑,可张九天、张九清近在咫尺,一个错步便能封喉断脉。
他眼角余光扫见张九天左足微旋,不丁不八,拂尘梢尖悄然离臂,蓄势待发。
电光石火间,他斜身滑步,让开锋刃,顺势后撤半步,撞进薄近侯胸前破绽,借力一送,力道巧如抽丝。
薄近侯热血冲顶,脚下虚浮,被这一撞踉蹌倒退,噔噔噔连退三步,身子还没站稳,忽觉手腕一沉——顾天白已侧身探手,稳稳托住斧柄,千钧之力被他单臂接下,也剎住了薄近侯溃散的势子。
前后不过眨眼工夫,顾天白已挪步贴至薄近侯身侧,两拨人马就此隔门对峙,一在檐下,一在阶前,相距丈余,气息胶著。
“顾天公子好功夫。”张九天抱拳含笑,略一俯首,礼数周全,挑不出半分疏漏。
顾天白不接话,只將巨斧轻轻搁地,反手扣住薄近侯腕后命门,一股绵劲透入,瞬间卸尽他一身蛮横气力。
昨夜偷听来的只言片语此刻浮上心头——原来他们寻的,正是自己。
终究没藏住,被人循跡找上门来。
他默然垂眸,姐姐却已缓步而出,指尖掸去蓍草茎叶沾的泥星,笑意淡淡:“方才閒坐卜卦,得『利东方』之象,果然紫气盈庭,贵客登堂。”
“顾二小姐安好。”张九天再度躬身。
“尚可。您便是九天道长?”姐姐语气平和,礼数不乱。
张九天抬眼望去,见她清秀面容上双目空茫,当年传闻果真不虚,心底轻嘆一声,只道:“正是贫道。”
姐姐脚步微顿,恰停在薄近侯身前,抬眼望向张九天:“不知道长此来,所为何事?”
名门教养刻在骨子里,举止从容,不卑不亢。
一问一答之间,张九天暂且压下对那持斧少年突袭的疑虑,先作揖答道:“贫道与师妹张九清奉师命游方,途经歷下,听徒孙说起二小姐与三公子在此棲身,特来拜会,叨扰之处,万望见谅。”言罢又是一礼,端方守矩,无可指责。
姐姐唇角微扬,一声轻笑似风掠竹:“佛门弟子,敢打妄语么?这话一出口,便落了邪见——拜不得无上师宝,修不了玄中大道。”
这次张九天却沉默了,只把笑意堆在脸上,静静望著姐姐。
姐姐压根没指望他接话——她这番话里裹著冰碴子,字字带刺,句句含锋,分明是拿话当鞭子抽人。
但凡有点脑子的,谁肯往这刀尖上撞?
她紧接著又道:“依我所知,九天道长与九清道长这对道门璧人,平日不是在紫禁城內开坛讲经,便是在圜丘台上焚香诵咒;
再不济,也该窝在武当藏书楼里翻那些泛黄髮脆的道藏典籍。
哪来的閒工夫,跑到歷下城这种地方溜达?
再说,眼下已入正月,朝廷年后头桩大事就是开朝大典,道长不赶回京城候命,倒有空来这儿虚耗光阴?九天道长別绕弯子了,有话痛快撂出来便是。”
张九天仍只噙著笑,任她说完,也不辩解。张九清却按捺不住,火气直衝脑门,冷喝一声:“小丫头片子,嘴倒是利索!”
姐姐耳朵轻轻一抖,笑著接腔:“哟,九清道长也在啊?果然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形影不离得很。可我跟九天道长说话,您插哪门子嘴?
出嫁从夫的道理都拎不清,三从四德怕是连边儿都没沾过吧?
难不成还得我这未嫁闺女,手把手教您规矩?”
“你……”张九清一时语塞,刚要发作,却被张九天一挥拂尘拦住。
他这才缓步上前,接过话头:“顾二小姐说得极是,是贫道俗气了。实因前几日山中接到徒孙密报,说似见二小姐与三公子现身歷下,拿捏不准真假,这才劳烦我们夫妻走这一趟,只为当面確认。”
“確认完了?”姐姐眼尾微扬,明知故问。
张九天呵呵一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得回山復命,去向张九鼎稟报了?”
他依旧含笑不语。
“再然后,是不是就要把我和弟弟的消息,散到江湖各处去?尤其要让那位你们连提都不敢大声提的人物,第一时间听见风声?”
张九天心头一凛——这姑娘哪只是伶牙俐齿,分明是听风辨位、见影知形,自己才吐半句,她已把后头七八步全踩准了。
此刻站在她面前,竟像被剥了壳的核桃,里外通透,毫赤裸裸。
於是,他还是笑。
“好,隨你们怎么安排,我也拦不住。不过在这之前,小女子想跟道长討个商量。”
张九天略一怔神,拱手道:“顾二小姐请讲。”
“九天道长可晓得,我姐弟二人,与贵派弟子韩有鱼之间,还横著一桩旧帐?”
张九天神色微动,恍然道:“原来如此。贫道此来,正为此事。是门下弟子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小姐,特地带他登门赔罪,万望二小姐宽宥。”
说著,抬手示意自始至终垂首肃立、未曾开口的韩有鱼上前。
可怜韩有鱼,前日被张九清一掌劈得臥床整整两昼夜,刚能下地,又被拖来此处——他万没想到,这对煞星竟就住在离自己不过两条街的地方。
进门还没摸清状况,就被一个膀大腰圆、拎著丈许长斧的少年兜头劈来,险些把魂嚇飞。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喊一声冤。
“九天道长误会了。”姐姐不等韩有鱼迈步,便伸手拦下,“我这人心宽似海,翻篇的事早翻过去了,赔什么礼?
可您这位徒孙,还干了一件更扎眼的勾当,您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