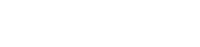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54章 我信你,不会害人
“九清?九天?谁啊?”薄近侯一脸茫然。
顾天白懒得跟薄近侯多费唇舌,直接扭头问姐姐:“这两人跑这儿来干啥?”
姐姐想得比弟弟深得多。哪怕早料到几分端倪,也怕他钻牛角尖胡思乱想,索性闭了嘴,只淡淡道:“腿长在人家身上,爱往哪儿蹽,谁拦得住?”
薄近侯耳朵尖,听出话里裹著刺,眉头一拧:“你们认得他们?”
顾天白本就对薄近侯存著几分难以言说的歉意,此刻更觉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倒是姐姐搁下那块油亮嫩滑的鸭胸肉,不紧不慢接了话:“武当山来的两个道士。”既答了薄近侯的问,又把交情藏得严严实实。
薄近侯信了,压根没往別处琢磨,只当是唬他玩儿的,冷哼一声:“武当的又如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说到最后“偿命”二字,声音反倒泄了劲,可眼里那股子狠劲却烧得灼人——连顾天白都忍不住暗暗点头。
人活著,总得攥著点东西往前奔。
可这是血债,不是口角。顾天白想劝,又怕词不达意,反添堵。那种至亲猝然抽离的滋味,他尝过。
人间最熬人的是活別,最剜心的是永诀。
刚失去时,疼是钝的;往后某天冷不丁想起一句笑、一个背影,那痛才真正扎进骨头缝里。
姐姐没再开口,只从沉默里咂摸出些门道,低头慢条斯理啃著酥脆流油的鸭架子。
薄近侯心头压著事,连带那只燉得滚烂的肥鸭也失了神采。
姐姐这老饕舌头刁得很,夹两块最细嫩的鸭脯便撂了筷,光捧碗喝汤——比起昨日那只泥巴鸡,差了不止一截。
薄近侯自己也是食不知味,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嚼半晌才囫圇咽下。
倒衬得顾天白格外敞亮:有酒有肉,便是人间快活。
饭毕,作息如钟錶般准的姐姐去歇午觉。顾天白便陪薄近侯练那套尚显生涩、却已初具轮廓的三板斧。
仇人就在眼皮底下,偏动不得手——薄近侯这一下午,硬是把空荡荡的院子劈出了风雷声。
斧锋所向,劈则裂空,撩则撕云,每一记都似要把天地劈开一道口子。
顾天白没拦。这样也好。
怨气散了,人才稳得住;若闷在肚子里发酵,迟早酿成偏执的疯火。
他没想到的是,这般倾力发泄,竟让招式也活泛起来,一招一式愈发沉实凌厉,事半功倍。
两个时辰过去,日头斜斜滑进远处楼檐后,薄近侯喘著粗气收势。这一下午的苦练,成效惊人。
顾天白不得不承认:这副筋骨,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虽比不上那些经年累月捶打出来的老江湖,但寻常武林人撞上他,怕是要当场栽个大跟头。
暮色渐浓,薄近侯隨手將巨斧往地上一摜,朝姐弟俩草草抱拳就要走——折腾半天,心口那团鬱结,终究没鬆开。
门槛上歪坐著的姐姐忽然开口:“千年前庄子说过,『復仇者不折鏌鋣,虽有忮心,不怨飘瓦』。懂这话么?”
这话不知冲谁问的。
其实也不必点名——她太清楚自己这个弟弟:从小见了秘籍就皱眉,哪会琢磨这些拗口的老话?至於薄近侯,这几日打交道下来,她早看清了他肚里几两墨水。
所以她根本没等回应,径直解道:“报仇的人,不会折断伤了自己的宝剑;心里再恨,也不会怪罪无意砸来的瓦片。”
“嗯?”两人听懂了,却又愣住了。
明明前些日子,还是她推著薄近侯往前走;怎么如今,倒说起这等劝退的话?
“全是放狗屁!”姐姐忽地啐了一口,“真都这么想,这世道早塌成渣了!”
“我盼著啊,这恨意別糊了你的眼、乱了你的心,倒要化作悬在头顶的利刃,时时逼你精进。”
“心存芥蒂,飞瓦皆成仇。”
也不知是兴致阑珊,还是心头压了块石头,这几日薄近侯来得格外迟——日头爬过屋脊才拖著步子晃进门,眼皮浮肿,眼底青灰,活像熬了整宿没合眼。
那日撞见韩有鱼,怕是真戳中了他最痛的软肋。
难为他了。这般血海深仇,仇人就在眼皮底下晃荡,连名字都清清楚楚,自己却连根汗毛都动不得。换谁心里不烧得发烫?
这是死结,越解越紧,顾天白也懒得劝。生撕的仇、刻骨的恨,哪是几句宽慰能熨平的?
薄近侯进门便闷声不响,盘腿调息一阵,接著抄起那把沉甸甸的巨斧,呼呼抡开,斧风颳得落叶打旋。
姐姐早听见他踏院门的动静,见他不开口,心里便透亮了,忽然觉得眼前这少年单薄得可怜——姨娘一走,世上再没一个牵著他衣角的人。
自己待他冷淡些,是不是真有些过分?
可转念又一摇头,仿佛要把这念头甩出耳外,暗笑自己何时变得这般婆婆妈妈。
天下之大,她与弟弟早已浪跡四方,偶施援手已是本分,若还犹犹豫豫、反覆掂量,倒不像她了。
“瞧他练得如何?”姐姐压低声音问。
顾天白蹲在廊下,目光懒懒追著斧影,眼皮都不抬,“不错。”
答得隨意,像隨口应一声风声。
“你光夸,好不好可由不得你定。我又看不见,怎知你不是哄我?”
姐姐语里带点无可奈何。
顾天白偏过头,见她微噘著嘴,眉梢含嗔,忍不住弯了嘴角,“真不赖,寻常江湖客,近身三步就得栽跟头。”
“照你这么说,他一夜之间就登峰造极了?”姐姐笑著打趣。
顾天白嗤地一笑,“那还了得?”
姐姐从鞦韆上跃下,裙裾一挽,蹲到弟弟身边,也不避著薄近侯,直截了当道:“你可曾琢磨过,我为何偏要你教他功夫?”
顾天白仍望著那斧影翻飞,神情却比往日鬆快几分,“不想琢磨。你定下的事,我照做便是。”他侧过脸,目光澄澈,“我信你,不会害人。”
姐姐伸手,稳稳落在他发顶,轻轻一揉,笑得眼尾微翘,“傻子。”
顾天白闭了嘴。
偌大天地,不过是你煮一壶茶,我听一句笑。
这样,就很好。
姐姐顺手扯下树根旁几茎野草,指尖慢条斯理地撕开,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说给弟弟听:“你性子我最清楚——打小护我护得紧,这几年隱姓埋名闯江湖,凡事总拦在我前头,生怕我沾半点麻烦。
可这次韩有鱼那膏粱子弟,当面折辱於我,我岂能再因武当那个不上檯面的轻狂小子,让你去蹚浑水、惹是非?”
“就当姐姐歇了三年,该磨磨这钝了的脑子了。”她目光空落落地停在院门方向,声音轻得像风掠过檐角,“不然,怎么对得起『遐邇八方』这四个字?”
似觉这话有趣,她喉间忽地滚出一串清脆笑声,如铃摇春枝。
顾天白望著姐姐出神,阳光温软,院中静得只余草叶轻颤。这样,真的很好。
“帮我看看这卦象。”姐姐忽道,自己看不见弟弟神色,也未留意脚下散落的蓍艾草茎。
顾天白这才发觉,她指尖捻草为爻,竟已排成一卦——这揲蓍法,源出上古大衍之数,不问姻缘仕途,只断吉凶祸福。
“是哪一卦?”他从小见惯姐姐閒来掐草推演,两仪三才、四象八卦轮番上阵,可他对这些向来无感,至今仍是一头雾水。
“初变阳爻,再变阴爻,三变復阳,积五茎为基,合三才之人位,得六数,大吉;卦属震,主生长,利东行。”
姐姐微微侧首,目光静静投向院门。
第454章 我信你,不会害人
“九清?九天?谁啊?”薄近侯一脸茫然。
顾天白懒得跟薄近侯多费唇舌,直接扭头问姐姐:“这两人跑这儿来干啥?”
姐姐想得比弟弟深得多。哪怕早料到几分端倪,也怕他钻牛角尖胡思乱想,索性闭了嘴,只淡淡道:“腿长在人家身上,爱往哪儿蹽,谁拦得住?”
薄近侯耳朵尖,听出话里裹著刺,眉头一拧:“你们认得他们?”
顾天白本就对薄近侯存著几分难以言说的歉意,此刻更觉喉咙发紧,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倒是姐姐搁下那块油亮嫩滑的鸭胸肉,不紧不慢接了话:“武当山来的两个道士。”既答了薄近侯的问,又把交情藏得严严实实。
薄近侯信了,压根没往別处琢磨,只当是唬他玩儿的,冷哼一声:“武当的又如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说到最后“偿命”二字,声音反倒泄了劲,可眼里那股子狠劲却烧得灼人——连顾天白都忍不住暗暗点头。
人活著,总得攥著点东西往前奔。
可这是血债,不是口角。顾天白想劝,又怕词不达意,反添堵。那种至亲猝然抽离的滋味,他尝过。
人间最熬人的是活別,最剜心的是永诀。
刚失去时,疼是钝的;往后某天冷不丁想起一句笑、一个背影,那痛才真正扎进骨头缝里。
姐姐没再开口,只从沉默里咂摸出些门道,低头慢条斯理啃著酥脆流油的鸭架子。
薄近侯心头压著事,连带那只燉得滚烂的肥鸭也失了神采。
姐姐这老饕舌头刁得很,夹两块最细嫩的鸭脯便撂了筷,光捧碗喝汤——比起昨日那只泥巴鸡,差了不止一截。
薄近侯自己也是食不知味,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嚼半晌才囫圇咽下。
倒衬得顾天白格外敞亮:有酒有肉,便是人间快活。
饭毕,作息如钟錶般准的姐姐去歇午觉。顾天白便陪薄近侯练那套尚显生涩、却已初具轮廓的三板斧。
仇人就在眼皮底下,偏动不得手——薄近侯这一下午,硬是把空荡荡的院子劈出了风雷声。
斧锋所向,劈则裂空,撩则撕云,每一记都似要把天地劈开一道口子。
顾天白没拦。这样也好。
怨气散了,人才稳得住;若闷在肚子里发酵,迟早酿成偏执的疯火。
他没想到的是,这般倾力发泄,竟让招式也活泛起来,一招一式愈发沉实凌厉,事半功倍。
两个时辰过去,日头斜斜滑进远处楼檐后,薄近侯喘著粗气收势。这一下午的苦练,成效惊人。
顾天白不得不承认:这副筋骨,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虽比不上那些经年累月捶打出来的老江湖,但寻常武林人撞上他,怕是要当场栽个大跟头。
暮色渐浓,薄近侯隨手將巨斧往地上一摜,朝姐弟俩草草抱拳就要走——折腾半天,心口那团鬱结,终究没鬆开。
门槛上歪坐著的姐姐忽然开口:“千年前庄子说过,『復仇者不折鏌鋣,虽有忮心,不怨飘瓦』。懂这话么?”
这话不知冲谁问的。
其实也不必点名——她太清楚自己这个弟弟:从小见了秘籍就皱眉,哪会琢磨这些拗口的老话?至於薄近侯,这几日打交道下来,她早看清了他肚里几两墨水。
所以她根本没等回应,径直解道:“报仇的人,不会折断伤了自己的宝剑;心里再恨,也不会怪罪无意砸来的瓦片。”
“嗯?”两人听懂了,却又愣住了。
明明前些日子,还是她推著薄近侯往前走;怎么如今,倒说起这等劝退的话?
“全是放狗屁!”姐姐忽地啐了一口,“真都这么想,这世道早塌成渣了!”
“我盼著啊,这恨意別糊了你的眼、乱了你的心,倒要化作悬在头顶的利刃,时时逼你精进。”
“心存芥蒂,飞瓦皆成仇。”
也不知是兴致阑珊,还是心头压了块石头,这几日薄近侯来得格外迟——日头爬过屋脊才拖著步子晃进门,眼皮浮肿,眼底青灰,活像熬了整宿没合眼。
那日撞见韩有鱼,怕是真戳中了他最痛的软肋。
难为他了。这般血海深仇,仇人就在眼皮底下晃荡,连名字都清清楚楚,自己却连根汗毛都动不得。换谁心里不烧得发烫?
这是死结,越解越紧,顾天白也懒得劝。生撕的仇、刻骨的恨,哪是几句宽慰能熨平的?
薄近侯进门便闷声不响,盘腿调息一阵,接著抄起那把沉甸甸的巨斧,呼呼抡开,斧风颳得落叶打旋。
姐姐早听见他踏院门的动静,见他不开口,心里便透亮了,忽然觉得眼前这少年单薄得可怜——姨娘一走,世上再没一个牵著他衣角的人。
自己待他冷淡些,是不是真有些过分?
可转念又一摇头,仿佛要把这念头甩出耳外,暗笑自己何时变得这般婆婆妈妈。
天下之大,她与弟弟早已浪跡四方,偶施援手已是本分,若还犹犹豫豫、反覆掂量,倒不像她了。
“瞧他练得如何?”姐姐压低声音问。
顾天白蹲在廊下,目光懒懒追著斧影,眼皮都不抬,“不错。”
答得隨意,像隨口应一声风声。
“你光夸,好不好可由不得你定。我又看不见,怎知你不是哄我?”
姐姐语里带点无可奈何。
顾天白偏过头,见她微噘著嘴,眉梢含嗔,忍不住弯了嘴角,“真不赖,寻常江湖客,近身三步就得栽跟头。”
“照你这么说,他一夜之间就登峰造极了?”姐姐笑著打趣。
顾天白嗤地一笑,“那还了得?”
姐姐从鞦韆上跃下,裙裾一挽,蹲到弟弟身边,也不避著薄近侯,直截了当道:“你可曾琢磨过,我为何偏要你教他功夫?”
顾天白仍望著那斧影翻飞,神情却比往日鬆快几分,“不想琢磨。你定下的事,我照做便是。”他侧过脸,目光澄澈,“我信你,不会害人。”
姐姐伸手,稳稳落在他发顶,轻轻一揉,笑得眼尾微翘,“傻子。”
顾天白闭了嘴。
偌大天地,不过是你煮一壶茶,我听一句笑。
这样,就很好。
姐姐顺手扯下树根旁几茎野草,指尖慢条斯理地撕开,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说给弟弟听:“你性子我最清楚——打小护我护得紧,这几年隱姓埋名闯江湖,凡事总拦在我前头,生怕我沾半点麻烦。
可这次韩有鱼那膏粱子弟,当面折辱於我,我岂能再因武当那个不上檯面的轻狂小子,让你去蹚浑水、惹是非?”
“就当姐姐歇了三年,该磨磨这钝了的脑子了。”她目光空落落地停在院门方向,声音轻得像风掠过檐角,“不然,怎么对得起『遐邇八方』这四个字?”
似觉这话有趣,她喉间忽地滚出一串清脆笑声,如铃摇春枝。
顾天白望著姐姐出神,阳光温软,院中静得只余草叶轻颤。这样,真的很好。
“帮我看看这卦象。”姐姐忽道,自己看不见弟弟神色,也未留意脚下散落的蓍艾草茎。
顾天白这才发觉,她指尖捻草为爻,竟已排成一卦——这揲蓍法,源出上古大衍之数,不问姻缘仕途,只断吉凶祸福。
“是哪一卦?”他从小见惯姐姐閒来掐草推演,两仪三才、四象八卦轮番上阵,可他对这些向来无感,至今仍是一头雾水。
“初变阳爻,再变阴爻,三变復阳,积五茎为基,合三才之人位,得六数,大吉;卦属震,主生长,利东行。”
姐姐微微侧首,目光静静投向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