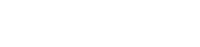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53章 真叫人费解
好不容易捱到今天,閒来无事,谁承想韩有鱼又捅出这么大篓子。
但凡长了眼睛的,都看得出张九清那张脸阴得能拧出水来——武当上下背地里喊她“母大虫”,可不是白叫的。
张九天本想寻那人问个明白,可眼下哪敢往枪口上撞?只得缩著脖子装哑巴,眼观鼻、鼻观心,权当没这回事。
张九天对韩有鱼向来不咸不淡,全因师兄面子才勉强点头应承;
说不上厌烦,却也绝不像师兄那样,把这徒孙当心头肉捧著、当亲孙儿宠著。
如今武当五代同堂,上字辈的老前辈们,或羽化登仙,或兵解留功,早不沾尘世烟火;
九字辈的师兄弟,十有八九闭关苦修,只盼临终前撞开一道天门,搏个虹化飞升的体面。
照理说,韩有鱼这月字辈外门弟子,压根没资格踏进山门习艺——他亲哥韩鯤鹏,也不过隔三岔五被內门长辈点拨两句罢了。
偏巧掌门张九鼎青眼有加,硬是把他抬进內门序列,视作己出。
可翻遍武当五代千余门人,真心喜欢韩有鱼的,怕是掰著手指头都数不满五个,还多半是碍於张九鼎的情面。
其余人嫌他浮浪、厌他骄纵、恼他不知轻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韩有鱼一个趔趄,膝盖差点磕在地上,硬生生挨了一记耳光,连喘气都憋著,更別提开口辩解。
上座的杨缠贯一瞧气氛绷得像拉满的弓弦,赶紧打个哈哈起身,脚底抹油溜向后院。刚拐过影壁,就听见那坤道女冠一声断喝:“跪下!”
“模样倒周正,脾气却比灶王爷还衝。”杨缠贯边走边腹誹,“也不知九天道长怎么日日吃得消。”
见杨缠贯闪人,那位坤道真人再按捺不住,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声如裂帛。
韩鯤鹏在一旁屏息垂首,大气不敢出,照样被扫了颱风尾。
可这火还没烧尽,连一向端坐如松、眼观鼻鼻观心的张九天,也被揪出来数落一通。
骂韩有鱼不成器,糟蹋武当千年清誉;骂韩鯤鹏失兄长之责,纵容弟弟胡来,搅得家风蒙尘;
最后矛头直指张九天——整日冷眼旁观,袖手不管,宗门事当儿戏,为师者岂能如此?
这一顿雷霆怒骂,震得整座宅子嗡嗡作响。
那些平日里只见过张九清寡言静默的女佣僕役,这回才算真正见识了这位女官发起火来,竟似火山喷涌,骇人至极。
等怒火泄尽,张九清虽收敛了逼人的煞气,眉宇间仍凝著寒霜。她冷冷盯著中堂里跪得狼狈不堪的韩有鱼,转头吩咐韩鯤鹏:“锁后院去,不许放出来。”
两人刚走远,张九天虽也被训得灰头土脸,心里却透亮得很。没急著劝,只缓声道:“你手太重了。”
话音未落,张九清眼底火苗又窜起半寸。张九天忙接一句:“宗门这些琐碎事,睁只眼闭只眼罢。烂摊子一堆,你管得过来?”
张九清气得指尖发颤:“这朽木你还要替他兜著?”
语气平平淡淡,可那眼神,刀锋似的刮在张九天脸上。
张九天望著眼前这位年过半百仍性烈如火的道侣,无奈一笑:“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力道也没收著——回头师兄知道了,又要念你。”
“哼!”她牙关咬紧,“他败坏我武当门风,触犯道门戒律,撞我手里,我还管不得了?”
张九天反倒神色轻鬆:“师兄都不伸手,咱们操哪门子心?”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清规戒律,拴得住有心向道的人。
外门这些孩子里,真守规矩的有几个?莫非你打算一个个拎出来,挨个敲打?”
张九清被张九天堵得一时失语,喉头滚动几下,竟吐不出半个字来。
他本想眼不见心不烦,可那股子火气偏在胸中横衝直撞,最后全数砸向屋里正歪在榻上闭目养神的韩有鱼——“真叫人费解!师兄当年究竟哪只眼睛瞧出这膏粱子弟是外门的指望?
別说他哥哥韩鯤鹏,单论我武当山外门,根骨更硬、机缘更厚、心性更稳的弟子比比皆是,怎偏把『幸』字压在这不成器的小子肩上?
这些年他道法寸步未进,倒把门风搅得乌烟瘴气,简直令人齿冷!”
张九天缓步上前,在张九清对面蒲团上端坐下来,声音温软如絮:“师兄所谋,非我等轻易揣度。或许另有深意,也未可知。”
张九清那股子烈火脾气,碰上张九天这团揉不散的棉花,竟也悄然熄了大半。他仰头长吁一口气,眉间沟壑却未舒展。
张九天又轻轻道:“罢了,旧事莫提。静坐几轮心法,调匀气息,怒气伤肝,伤身又误功。”
张九清应了一声,刚摆好坐姿,忽又抬眼:“当真没差?”
话没头没尾,可结髮数十载的张九天早已与他心意相通,只垂眸一笑:“九成九。”
问得含蓄,答得简净,彼此都懂。
“你说……师兄当真信了那句讖言?”张九清冷不丁又拋出一句,飘得毫无来由。
张九天微怔,旋即摇头:“纵使信了,这一家子又能翻出什么浪来?当年那人搅得江湖血雨腥风,尚且撼不动我武当山一根樑柱,如今还能掀得起多大风浪?”
“那师兄遣我们来,总不会只为验一验这小子是真是假吧。”
张九天沉默片刻,未应。
“难不成……真要把千载武当,拱手託付出去?”
张九天终於抬眼,正视这位同修数十载、相敬如宾的道侣。目光一沉,似有千钧压下。
几个呼吸之后,他缓缓吐纳,抬手轻拂尘柄,嗓音低而沉:“罢了,此事,非你我所能定夺。”
张九清静默良久,终是敛起满腹鬱气,也跟著嘆了一声,像是一声应和,又像一声认命。
薄近侯攥著鸭脖,面无波澜地跨进小院门槛。
终究才十八九岁,少年心性藏不住事,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连眉梢都绷著一股子闷劲。
顾天白素来不爱凑热闹,可见薄近侯蹲在墙角一声不吭地拔鸭毛,动作生狠,鸭子都快被薅禿了,便忍不住开口:“怎么了?”
姐姐玲瓏剔透,一听这话便知有异,也侧过脸来问:“出什么事了?”
薄近侯手上力道更重了几分,鸭毛簌簌往下掉,嘴里咬牙切齿:“我撞见韩有鱼了。”
顾天白心头一亮,顿时明白了。
“那就踏实练功,咬紧牙关练功,早一日精进,早一日替你姨娘雪恨。”
鞦韆上的姐姐语气平直,既无激愤,也无安抚,“与其干坐这儿憋气,不如去桩上站半个时辰——难不成气鼓鼓瞪半天,仇就自己飞上门来了?”
薄近侯抿著嘴不吭声,心里却晓得这话扎得准、戳得实。
顾天白反倒起了兴致:“怎会偏偏遇上他?”
薄近侯一边刮净鸭腹细绒,一边把方才出门撞见的情形细细道来。顾天白留意的,却是韩有鱼身旁那两人。
“你看见一位女冠?”姐姐忽然开口。
鸭子收拾利落,薄近侯已蹲在灶前点火添柴,听见问话愣了愣:“女冠?啥玩意儿?”
“女道士。”姐姐语气耐性十足,“道姑是民间俗唤,听著糙,道门中人並不爱听。”
“哦……”薄近侯点点头,“就是个穿兰衣的女道士,带著韩有鱼,还有一个男的。”
他压根不认识韩鯤鹏——这几日打探的全是韩有鱼的底细,旁人名字连影儿都没沾上。
顾天白望向姐姐,眼神里已有七八分篤定。武当山上能著兰衣的坤道,掰著指头也数得出一个。
姐姐略一思忖,指尖轻叩鞦韆扶手:“九清道长到了,九天道长,想必也在。”
第453章 真叫人费解
好不容易捱到今天,閒来无事,谁承想韩有鱼又捅出这么大篓子。
但凡长了眼睛的,都看得出张九清那张脸阴得能拧出水来——武当上下背地里喊她“母大虫”,可不是白叫的。
张九天本想寻那人问个明白,可眼下哪敢往枪口上撞?只得缩著脖子装哑巴,眼观鼻、鼻观心,权当没这回事。
张九天对韩有鱼向来不咸不淡,全因师兄面子才勉强点头应承;
说不上厌烦,却也绝不像师兄那样,把这徒孙当心头肉捧著、当亲孙儿宠著。
如今武当五代同堂,上字辈的老前辈们,或羽化登仙,或兵解留功,早不沾尘世烟火;
九字辈的师兄弟,十有八九闭关苦修,只盼临终前撞开一道天门,搏个虹化飞升的体面。
照理说,韩有鱼这月字辈外门弟子,压根没资格踏进山门习艺——他亲哥韩鯤鹏,也不过隔三岔五被內门长辈点拨两句罢了。
偏巧掌门张九鼎青眼有加,硬是把他抬进內门序列,视作己出。
可翻遍武当五代千余门人,真心喜欢韩有鱼的,怕是掰著手指头都数不满五个,还多半是碍於张九鼎的情面。
其余人嫌他浮浪、厌他骄纵、恼他不知轻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韩有鱼一个趔趄,膝盖差点磕在地上,硬生生挨了一记耳光,连喘气都憋著,更別提开口辩解。
上座的杨缠贯一瞧气氛绷得像拉满的弓弦,赶紧打个哈哈起身,脚底抹油溜向后院。刚拐过影壁,就听见那坤道女冠一声断喝:“跪下!”
“模样倒周正,脾气却比灶王爷还衝。”杨缠贯边走边腹誹,“也不知九天道长怎么日日吃得消。”
见杨缠贯闪人,那位坤道真人再按捺不住,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声如裂帛。
韩鯤鹏在一旁屏息垂首,大气不敢出,照样被扫了颱风尾。
可这火还没烧尽,连一向端坐如松、眼观鼻鼻观心的张九天,也被揪出来数落一通。
骂韩有鱼不成器,糟蹋武当千年清誉;骂韩鯤鹏失兄长之责,纵容弟弟胡来,搅得家风蒙尘;
最后矛头直指张九天——整日冷眼旁观,袖手不管,宗门事当儿戏,为师者岂能如此?
这一顿雷霆怒骂,震得整座宅子嗡嗡作响。
那些平日里只见过张九清寡言静默的女佣僕役,这回才算真正见识了这位女官发起火来,竟似火山喷涌,骇人至极。
等怒火泄尽,张九清虽收敛了逼人的煞气,眉宇间仍凝著寒霜。她冷冷盯著中堂里跪得狼狈不堪的韩有鱼,转头吩咐韩鯤鹏:“锁后院去,不许放出来。”
两人刚走远,张九天虽也被训得灰头土脸,心里却透亮得很。没急著劝,只缓声道:“你手太重了。”
话音未落,张九清眼底火苗又窜起半寸。张九天忙接一句:“宗门这些琐碎事,睁只眼闭只眼罢。烂摊子一堆,你管得过来?”
张九清气得指尖发颤:“这朽木你还要替他兜著?”
语气平平淡淡,可那眼神,刀锋似的刮在张九天脸上。
张九天望著眼前这位年过半百仍性烈如火的道侣,无奈一笑:“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力道也没收著——回头师兄知道了,又要念你。”
“哼!”她牙关咬紧,“他败坏我武当门风,触犯道门戒律,撞我手里,我还管不得了?”
张九天反倒神色轻鬆:“师兄都不伸手,咱们操哪门子心?”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来,“清规戒律,拴得住有心向道的人。
外门这些孩子里,真守规矩的有几个?莫非你打算一个个拎出来,挨个敲打?”
张九清被张九天堵得一时失语,喉头滚动几下,竟吐不出半个字来。
他本想眼不见心不烦,可那股子火气偏在胸中横衝直撞,最后全数砸向屋里正歪在榻上闭目养神的韩有鱼——“真叫人费解!师兄当年究竟哪只眼睛瞧出这膏粱子弟是外门的指望?
別说他哥哥韩鯤鹏,单论我武当山外门,根骨更硬、机缘更厚、心性更稳的弟子比比皆是,怎偏把『幸』字压在这不成器的小子肩上?
这些年他道法寸步未进,倒把门风搅得乌烟瘴气,简直令人齿冷!”
张九天缓步上前,在张九清对面蒲团上端坐下来,声音温软如絮:“师兄所谋,非我等轻易揣度。或许另有深意,也未可知。”
张九清那股子烈火脾气,碰上张九天这团揉不散的棉花,竟也悄然熄了大半。他仰头长吁一口气,眉间沟壑却未舒展。
张九天又轻轻道:“罢了,旧事莫提。静坐几轮心法,调匀气息,怒气伤肝,伤身又误功。”
张九清应了一声,刚摆好坐姿,忽又抬眼:“当真没差?”
话没头没尾,可结髮数十载的张九天早已与他心意相通,只垂眸一笑:“九成九。”
问得含蓄,答得简净,彼此都懂。
“你说……师兄当真信了那句讖言?”张九清冷不丁又拋出一句,飘得毫无来由。
张九天微怔,旋即摇头:“纵使信了,这一家子又能翻出什么浪来?当年那人搅得江湖血雨腥风,尚且撼不动我武当山一根樑柱,如今还能掀得起多大风浪?”
“那师兄遣我们来,总不会只为验一验这小子是真是假吧。”
张九天沉默片刻,未应。
“难不成……真要把千载武当,拱手託付出去?”
张九天终於抬眼,正视这位同修数十载、相敬如宾的道侣。目光一沉,似有千钧压下。
几个呼吸之后,他缓缓吐纳,抬手轻拂尘柄,嗓音低而沉:“罢了,此事,非你我所能定夺。”
张九清静默良久,终是敛起满腹鬱气,也跟著嘆了一声,像是一声应和,又像一声认命。
薄近侯攥著鸭脖,面无波澜地跨进小院门槛。
终究才十八九岁,少年心性藏不住事,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连眉梢都绷著一股子闷劲。
顾天白素来不爱凑热闹,可见薄近侯蹲在墙角一声不吭地拔鸭毛,动作生狠,鸭子都快被薅禿了,便忍不住开口:“怎么了?”
姐姐玲瓏剔透,一听这话便知有异,也侧过脸来问:“出什么事了?”
薄近侯手上力道更重了几分,鸭毛簌簌往下掉,嘴里咬牙切齿:“我撞见韩有鱼了。”
顾天白心头一亮,顿时明白了。
“那就踏实练功,咬紧牙关练功,早一日精进,早一日替你姨娘雪恨。”
鞦韆上的姐姐语气平直,既无激愤,也无安抚,“与其干坐这儿憋气,不如去桩上站半个时辰——难不成气鼓鼓瞪半天,仇就自己飞上门来了?”
薄近侯抿著嘴不吭声,心里却晓得这话扎得准、戳得实。
顾天白反倒起了兴致:“怎会偏偏遇上他?”
薄近侯一边刮净鸭腹细绒,一边把方才出门撞见的情形细细道来。顾天白留意的,却是韩有鱼身旁那两人。
“你看见一位女冠?”姐姐忽然开口。
鸭子收拾利落,薄近侯已蹲在灶前点火添柴,听见问话愣了愣:“女冠?啥玩意儿?”
“女道士。”姐姐语气耐性十足,“道姑是民间俗唤,听著糙,道门中人並不爱听。”
“哦……”薄近侯点点头,“就是个穿兰衣的女道士,带著韩有鱼,还有一个男的。”
他压根不认识韩鯤鹏——这几日打探的全是韩有鱼的底细,旁人名字连影儿都没沾上。
顾天白望向姐姐,眼神里已有七八分篤定。武当山上能著兰衣的坤道,掰著指头也数得出一个。
姐姐略一思忖,指尖轻叩鞦韆扶手:“九清道长到了,九天道长,想必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