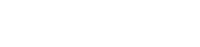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51章 大理寺不敢碰了
“东方日头红彤彤,出了个先生茅北空。鹤立鸡群笑伏龙,群鸟飞过问雌雄。”
茅南行,號北空先生,国子杏坛寺大祭酒。
说的人隨口一哼,听的人汗毛倒竖。大理寺卿正为茅南行惹来的塌天麻烦焦头烂额,冷不丁听见“伏龙”二字,心里咯噔一下——寻常百姓哪敢嚼这个字?
更別说“伏”字压在“龙”上,这不是往刀尖上舔血么?
寺里一位主簿,恰是茅南行亲传弟子,听罢只当玩笑,隨口道:“我老师早年写过一首赠別诗,送的是辞官归隱的老同僚——”
莫在清时恼不同,嘆君与吾各西东。
仙鹤不曾向蛰龙,群鸟怎知是雌雄。
大理寺卿日日伴君如伴虎,一听“蛰龙”二字,手心顿时沁出冷汗——管它诗中真意如何,“蛰龙”二字搁在当下,就是一颗隨时会炸的雷。
他再不敢耽搁,连夜將打油诗与原诗一併呈进宫去。
此时天子也正窝著火——內廷搜出一只鼻烟壶。
圣上是谁?那是火眼金睛、洞若观火的主儿。
鼻烟壶这物件,雅则雅矣,却偏偏是茅南行隨身不离的宝贝,朝野上下谁人不知?
消息像长了翅膀,眨眼间飞遍六宫。
甭管高位嬪妃是否知情,单是“一代大儒欺压弱女”这一条,已足够让宫墙內外嚼碎舌头。
风向彻底翻转。大理寺递上的摺子里,那首藏著“蛰龙”的诗,更是被解读成影射天子、动摇国本的逆言。
环环相扣,层层设套,乾净利落得令人胆寒。
天子扫一眼便明白:这局,是衝著谁布的,又是谁的手笔。
大理寺不敢碰了,皇上只得另派心腹彻查。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再想想那位行事如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顾家姑娘,结果自然呼之欲出。
风声还没平,坊间又爆出猛料:那位清高自詡的大祭酒,竟被撞见召妓狎玩。
茅南行气急攻心,当场呕血,臥床不起。
天子对顾家这丫头也是又气又服,嘴上斥了几句,转头便寻了个由头——“年迈体弱,宜赴外州静养”,明著贬官,实则调任上州別驾,悄悄把这场风波摁进了尘土里。
区区几步閒棋,便叫一个从四品大员灰头土脸滚出京城。谁能想到,布下此局的,竟是个尚未及笄的少女?
起因,不过是替弟弟討一口气。
可这玲瓏心思,偏只肯为弟弟铺路;哪怕换成自家那个老父亲遇上棘手事,姐姐也只推说太阳穴突突跳,半点不肯伸手搭一把。
更別提薄近侯——才见了几面的外人罢了。
姐姐命他教薄近侯武艺,助其手刃顾天白,这事至今叫韩有鱼摸不著头脑。
可依她那副冷硬脾性,怕是也就点到为止,再不会多费一分心力。
往后江湖阔远,山高水长,彼此擦肩,真不必再碰面。
韩有鱼越想越觉晦气——跟哥哥踏进歷下城,简直撞上了八辈子的霉运。
打从初二那日进城起,诸事不顺:饭食不对味、马蹄铁鬆了三次、连赌钱都连输七把。
今儿好不容易瞅准空子溜出来,满心盘算著寻点快活,刚被平康北里几个身段妖嬈、笑语娇嗔的姑娘簇拥著拽进楼门,正眉飞色舞,竟全没察觉街角处那位师叔祖,眼底已烧起两簇青白焰火。
直到屋里那个柳腰桃腮的姑娘掩唇低语:“楼下有个女道士在等。”
韩有鱼才猛地一僵,偷偷掀帘一瞥——果见张九清立在斜阳里,素衣如霜,脊背绷得笔直,纵是闭著眼,周身那股子寒气也压得路人纷纷侧目、窃窃指点。
她身子微微发颤,单薄得像根绷紧的弦。
“完了。”韩有鱼后颈发凉,腿肚子打软。
他在家怎么胡闹都行,可当著师门长辈的面干这等腌臢事?
別说胆子再肥,骨头缝里都透著怂。
说到底,他终究在意师门眼里自己是个什么模样。
当下哪还顾得上屋里人,一把推开那早已按捺不住、急欲翻身上马的玉脂尤物,扒开窗缝,屏息盯著楼下那人影。
见张九清转身离去,韩有鱼虽不知她要去哪儿,但心里清楚:这乐子,算是彻底泡汤了。
他抄起外衫便往外奔,身后女子一边系带一边咬牙啐骂。
火气未消,慾念未散,只被那一眼惊得缩回肚子里,可四下鶯声燕语、脂粉熏蒸,又勾得他浑身躁热。
他狠狠搓了搓掌心,牙关一咬,似下了狠心,左右一扫,抬脚拐进了隔壁另一座朱漆小楼。
张九清面色阴沉,眉峰拧成一道深壑。
一个坤道女冠,立在青楼门前任人指戳,体面早被踩进泥里。
她到底是女子,闯不得,走又不甘——那不成器的徒孙滑得像条泥鰍,抓不住,也丟不起这个人。
思来想去,只得回去搬韩鯤鹏来收拾烂摊子。
韩鯤鹏此刻脑仁嗡嗡作响。弟弟才安分几日?
原以为师叔祖只歇一两日,见见那来歷不明的姐弟便返山,谁料这小子胆大包天、眼皮子底下就敢胡来,偏还撞在张九清刀口上!
他好色之名早传遍山门,可被师长当场逮住,还是头一遭——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这一闹,怕是连爹都要被山中长老拎去训话。
他挨了女师叔祖几句冷言,便垂首缩肩跟著张九清往城北烟花巷去,一路提心弔胆,生怕一句话错、一步走歪,惹得师叔祖心头那团火,全烧到自己脸上。
韩鯤鹏心里也堵得慌:若真把弟弟惹毛了,回家哭天抢地告一状,爹娘少不得怪他看管不严;可若空手而归,张九清那口气,怕是全得衝著他撒。
两头掂量,倒觉得挨爹娘一顿数落,反倒轻省些。
早知如此,就不该带这混帐来!韩鯤鹏暗自磨牙。
张九清抬手指向那座青楼,韩鯤鹏硬著头皮往前凑。
他相貌本就出眾,还没走近,就被一群浓香扑鼻、笑靨如花的姑娘围了个密不透风。
他左拨右挡,挤出一条缝,声音发紧:“可瞧见一位穿粗麻衫、腰间別著白纸扇的公子?”
听见来人是找人的,不是寻欢的,满屋子姑娘立马收了笑顏,像被霜打蔫的花儿似的,各自耷拉著脸散开了。
韩鯤鹏眼疾手快,一把攥住离自己最近那个妖里妖气的女子手腕,伸手探进怀里摸出块鸽卵大小的碎银,“啪”地塞进她胸口,语气焦躁:“少囉嗦,快说!”
那银子沉甸甸砸进怀里,女子眉梢一挑,不快顿时化作三分笑意,腰肢一扭,双手往胸前一抱,把那对饱满丰盈托得更显挺翘,懒洋洋道:“那位公子进门没坐热凳子就溜了。
我家小翠都贴到他袖口了,他倒好,眼观鼻、鼻观心,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莫不是身子骨虚,中看不中用?”话音未落,自己先咯咯笑开了,笑声又软又浪。
“走了?”韩鯤鹏一怔,眉头拧紧,“往哪儿去了?”
女子斜睨一眼那银子,朝街对面一家招牌褪色的青楼扬了扬下巴:“喏,那儿。”
韩鯤鹏鬆手转身,袍角一甩,大步流星去了。
此刻韩有鱼刚收场,还搂著怀里温香软玉,半眯著眼,似醉非醉,指尖正摩挲著女人那对浑圆如碗、细嫩如脂的胸脯,好歹压住了连日来的焦躁与憋闷。
身下女子也懂火候,眼波流转,唇角含春,勾得他心头又窜起一把火,手劲加重,脸上浮起坏笑——方才的事早拋到九霄云外,正要翻身跨上,忽听门外一阵喧譁。
第451章 大理寺不敢碰了
“东方日头红彤彤,出了个先生茅北空。鹤立鸡群笑伏龙,群鸟飞过问雌雄。”
茅南行,號北空先生,国子杏坛寺大祭酒。
说的人隨口一哼,听的人汗毛倒竖。大理寺卿正为茅南行惹来的塌天麻烦焦头烂额,冷不丁听见“伏龙”二字,心里咯噔一下——寻常百姓哪敢嚼这个字?
更別说“伏”字压在“龙”上,这不是往刀尖上舔血么?
寺里一位主簿,恰是茅南行亲传弟子,听罢只当玩笑,隨口道:“我老师早年写过一首赠別诗,送的是辞官归隱的老同僚——”
莫在清时恼不同,嘆君与吾各西东。
仙鹤不曾向蛰龙,群鸟怎知是雌雄。
大理寺卿日日伴君如伴虎,一听“蛰龙”二字,手心顿时沁出冷汗——管它诗中真意如何,“蛰龙”二字搁在当下,就是一颗隨时会炸的雷。
他再不敢耽搁,连夜將打油诗与原诗一併呈进宫去。
此时天子也正窝著火——內廷搜出一只鼻烟壶。
圣上是谁?那是火眼金睛、洞若观火的主儿。
鼻烟壶这物件,雅则雅矣,却偏偏是茅南行隨身不离的宝贝,朝野上下谁人不知?
消息像长了翅膀,眨眼间飞遍六宫。
甭管高位嬪妃是否知情,单是“一代大儒欺压弱女”这一条,已足够让宫墙內外嚼碎舌头。
风向彻底翻转。大理寺递上的摺子里,那首藏著“蛰龙”的诗,更是被解读成影射天子、动摇国本的逆言。
环环相扣,层层设套,乾净利落得令人胆寒。
天子扫一眼便明白:这局,是衝著谁布的,又是谁的手笔。
大理寺不敢碰了,皇上只得另派心腹彻查。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再想想那位行事如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顾家姑娘,结果自然呼之欲出。
风声还没平,坊间又爆出猛料:那位清高自詡的大祭酒,竟被撞见召妓狎玩。
茅南行气急攻心,当场呕血,臥床不起。
天子对顾家这丫头也是又气又服,嘴上斥了几句,转头便寻了个由头——“年迈体弱,宜赴外州静养”,明著贬官,实则调任上州別驾,悄悄把这场风波摁进了尘土里。
区区几步閒棋,便叫一个从四品大员灰头土脸滚出京城。谁能想到,布下此局的,竟是个尚未及笄的少女?
起因,不过是替弟弟討一口气。
可这玲瓏心思,偏只肯为弟弟铺路;哪怕换成自家那个老父亲遇上棘手事,姐姐也只推说太阳穴突突跳,半点不肯伸手搭一把。
更別提薄近侯——才见了几面的外人罢了。
姐姐命他教薄近侯武艺,助其手刃顾天白,这事至今叫韩有鱼摸不著头脑。
可依她那副冷硬脾性,怕是也就点到为止,再不会多费一分心力。
往后江湖阔远,山高水长,彼此擦肩,真不必再碰面。
韩有鱼越想越觉晦气——跟哥哥踏进歷下城,简直撞上了八辈子的霉运。
打从初二那日进城起,诸事不顺:饭食不对味、马蹄铁鬆了三次、连赌钱都连输七把。
今儿好不容易瞅准空子溜出来,满心盘算著寻点快活,刚被平康北里几个身段妖嬈、笑语娇嗔的姑娘簇拥著拽进楼门,正眉飞色舞,竟全没察觉街角处那位师叔祖,眼底已烧起两簇青白焰火。
直到屋里那个柳腰桃腮的姑娘掩唇低语:“楼下有个女道士在等。”
韩有鱼才猛地一僵,偷偷掀帘一瞥——果见张九清立在斜阳里,素衣如霜,脊背绷得笔直,纵是闭著眼,周身那股子寒气也压得路人纷纷侧目、窃窃指点。
她身子微微发颤,单薄得像根绷紧的弦。
“完了。”韩有鱼后颈发凉,腿肚子打软。
他在家怎么胡闹都行,可当著师门长辈的面干这等腌臢事?
別说胆子再肥,骨头缝里都透著怂。
说到底,他终究在意师门眼里自己是个什么模样。
当下哪还顾得上屋里人,一把推开那早已按捺不住、急欲翻身上马的玉脂尤物,扒开窗缝,屏息盯著楼下那人影。
见张九清转身离去,韩有鱼虽不知她要去哪儿,但心里清楚:这乐子,算是彻底泡汤了。
他抄起外衫便往外奔,身后女子一边系带一边咬牙啐骂。
火气未消,慾念未散,只被那一眼惊得缩回肚子里,可四下鶯声燕语、脂粉熏蒸,又勾得他浑身躁热。
他狠狠搓了搓掌心,牙关一咬,似下了狠心,左右一扫,抬脚拐进了隔壁另一座朱漆小楼。
张九清面色阴沉,眉峰拧成一道深壑。
一个坤道女冠,立在青楼门前任人指戳,体面早被踩进泥里。
她到底是女子,闯不得,走又不甘——那不成器的徒孙滑得像条泥鰍,抓不住,也丟不起这个人。
思来想去,只得回去搬韩鯤鹏来收拾烂摊子。
韩鯤鹏此刻脑仁嗡嗡作响。弟弟才安分几日?
原以为师叔祖只歇一两日,见见那来歷不明的姐弟便返山,谁料这小子胆大包天、眼皮子底下就敢胡来,偏还撞在张九清刀口上!
他好色之名早传遍山门,可被师长当场逮住,还是头一遭——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这一闹,怕是连爹都要被山中长老拎去训话。
他挨了女师叔祖几句冷言,便垂首缩肩跟著张九清往城北烟花巷去,一路提心弔胆,生怕一句话错、一步走歪,惹得师叔祖心头那团火,全烧到自己脸上。
韩鯤鹏心里也堵得慌:若真把弟弟惹毛了,回家哭天抢地告一状,爹娘少不得怪他看管不严;可若空手而归,张九清那口气,怕是全得衝著他撒。
两头掂量,倒觉得挨爹娘一顿数落,反倒轻省些。
早知如此,就不该带这混帐来!韩鯤鹏暗自磨牙。
张九清抬手指向那座青楼,韩鯤鹏硬著头皮往前凑。
他相貌本就出眾,还没走近,就被一群浓香扑鼻、笑靨如花的姑娘围了个密不透风。
他左拨右挡,挤出一条缝,声音发紧:“可瞧见一位穿粗麻衫、腰间別著白纸扇的公子?”
听见来人是找人的,不是寻欢的,满屋子姑娘立马收了笑顏,像被霜打蔫的花儿似的,各自耷拉著脸散开了。
韩鯤鹏眼疾手快,一把攥住离自己最近那个妖里妖气的女子手腕,伸手探进怀里摸出块鸽卵大小的碎银,“啪”地塞进她胸口,语气焦躁:“少囉嗦,快说!”
那银子沉甸甸砸进怀里,女子眉梢一挑,不快顿时化作三分笑意,腰肢一扭,双手往胸前一抱,把那对饱满丰盈托得更显挺翘,懒洋洋道:“那位公子进门没坐热凳子就溜了。
我家小翠都贴到他袖口了,他倒好,眼观鼻、鼻观心,连根手指头都没动——莫不是身子骨虚,中看不中用?”话音未落,自己先咯咯笑开了,笑声又软又浪。
“走了?”韩鯤鹏一怔,眉头拧紧,“往哪儿去了?”
女子斜睨一眼那银子,朝街对面一家招牌褪色的青楼扬了扬下巴:“喏,那儿。”
韩鯤鹏鬆手转身,袍角一甩,大步流星去了。
此刻韩有鱼刚收场,还搂著怀里温香软玉,半眯著眼,似醉非醉,指尖正摩挲著女人那对浑圆如碗、细嫩如脂的胸脯,好歹压住了连日来的焦躁与憋闷。
身下女子也懂火候,眼波流转,唇角含春,勾得他心头又窜起一把火,手劲加重,脸上浮起坏笑——方才的事早拋到九霄云外,正要翻身跨上,忽听门外一阵喧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