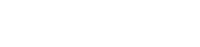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50章 四品大祭酒
正因如此,国子杏坛寺应运而生,成了天下俊彦的匯聚之地。
四书五经、性理算术、诸子百家,处处辩声琅琅;最盛时,连儒教祖庭兗州城外那座千年杏坛,都比不上京城这座新庙里的学风炽烈。
坊间甚至传著一句俏皮话:“杏坛枝头踩断枝,书声压过钟鼓鸣。”
也正因地位超然,歷任大祭酒,无一不是目高於顶的硕儒。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此话不假——建寺五十多年,四任大祭酒,个个傲骨嶙峋,连皇亲国戚登门,也得先递名帖、候通稟。
久而久之,便养出一种惯常的睥睨:仿佛天地间道理,尽在他们袖中卷里。
尤其那位前任大祭酒茅南行,留著一撮山羊鬍,整日鼻孔朝天,走路带风,见谁都像欠他三吊钱。
那天纯属巧合。顾天白素来见书就犯困,平日绕著杏坛寺走,生怕沾上半点墨气。
可那日不知怎的,脚下一拐,竟直奔寺门而去。
仗著在皇城里混了个熟脸,他连腰牌都没掏,就大摇大摆进了这等閒人不得擅入的禁地。
偏巧撞上茅南行——那老头正无所事事,在讲堂间踱著方步。
见他没文书、无引荐,当即沉下脸,厉声呵斥几句,旋即挥手撵人:“哪儿来的野小子?滚出去!”
顾天白本懒得跟这个把律令条文当祖宗牌位供著、拿规矩二字压人喘不过气的老学究多费口舌,抬脚就走。
谁知那老头儿竟追出门外,当场冲守门兵丁横眉竖目,劈头盖脸骂他们失职放进了个“来路不明的野人”。
这倒也罢了——顾天白自觉理亏,毕竟自己仗著几分熟脸,连腰牌都未掏便晃进了这座在西亳百姓眼里堪比宫禁森严的国子杏坛寺。
他心想,这老祭酒多半心里门清:自己虽没官身,但在城里也算掛得上號的人物,人家睁只眼闭只眼,原是给个薄面。
可谁料他刚依言退出杏坛寺大门,那老头儿反倒火上浇油,话里藏针,句句往守卫身上戳,末了竟扬言要递摺子进宫,参这几个门房“瀆职怠慢、不堪任用”,非要摘了他们的差事不可。
顾天白心头一沉,火苗子直往上窜——倒不是怕他告状,而是怕真惹出祸来,让几个老实巴交的兵卒丟了饭碗。
他强压怒意,只上前分辩几句,替那几个被指著鼻子骂的守卫说了两句公道话。就算真被革了职,大不了他亲自去吏部打个招呼,调去城防营或太僕寺做个閒差,总好过在这儿被人当街踩进泥里。
哪知那老祭酒得了势便翻脸不认人,手指几乎戳到顾天白鼻尖,一张嘴全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训斥;
接著又抖著鬍子,咬牙切齿念什么“欲求必达,欲禁必止,欲令必行”,活像背书背岔了气;
更扯出“朽木不可雕”那一套,再配上他那撮被学生暗讽为“牛尾巴毛”的山羊鬍,一边捋一边嘆世风日下,说什么“这般少年蔑法轻律,迟早误国殃民”。
满口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如泼水般倾泻而出——別说那几个只识得刀柄上刻字的守卫听得两眼发直,就连自小被爹娘按在书案前硬灌四书五经的顾天白,听著他那腔调,都差点以为自己偷了太庙香灰、砸了圣旨匣子。
顾天白本打定主意不搭理这尊活规矩碑,偏生那老头儿越说越亢奋,在门口跳脚嚷嚷,活似唱大戏,动静大得连本在街对麵茶楼包间里等他的姐姐都听见了。
旁人或许不知,可姐姐对顾天白那份护短劲儿,早已刻进骨头缝里——四品大祭酒?
她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若真有哪位天子开口挑弟弟半句毛病,这位从小把“护弟即护家”当信条的姐姐,怕是要当场掀了龙椅扶手才肯罢休。
更不用旁人添柴加火。
单瞧那老祭酒指著顾天白破口大骂的模样,活脱脱一个市井泼妇叉腰开骂,连唾沫星子都快溅到弟弟衣领上——姐姐哪里忍得?
三步並作两步上前,脸上还带著平日对祭酒毕恭毕敬的笑意,话却一句比一句扎得准、问得狠:先绕著弯子探他为何发难,再从他话缝里揪出破绽,最后只拎出一条——堂堂国子杏坛寺门前,你一个主官当街咆哮、惊扰学子、搅乱讲学,这算哪门子持重?
老祭酒顿时语塞,手指哆嗦著点了几下,终究憋出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甩袖而去,撂下狠话要去御前告状,非要把这个“目无纲常、胆大妄为”的丫头治个重罪。
可姐姐何曾把这种虚张声势放在眼里?她连眼皮都没抬,只望著那老头儿气冲冲奔向皇城的背影,嘴角微扬,仿佛看的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只扑火的飞蛾。
你以为这事就这么揭过了?
顾天白太了解姐姐——当眾让祭酒顏面扫地,不过是替弟弟挣回一口气;可弟弟被人指著鼻子羞辱,这口气若不一口口討回来,她夜里都睡不踏实。
姐姐回府后即刻动笔列单子,连夜摸清老祭酒平日爱喝什么茶、见客穿哪件袍子、连他书房窗朝哪边开都记在册上;
次日一早,借著给太后送新焙的云雾松针茶之机,混入宫城內院,在冷香亭拐角处“不小心”遗落一只青玉鼻烟壶;
转头又遣心腹去南曲巷头的醉仙楼,请了一位素有才名的校书娘,专挑老祭酒归宅时辰,在他朱漆大门前来回踱步,裙裾轻摆,笑语隱约,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
紧跟著,她命人搜罗齐老祭酒歷年刊印的诗稿、讲义、批註,彻夜未眠,红笔密密圈点,在每页空白处批下犀利评语,字字如刀,句句见血。
这句“先发制人,后发受制”的江湖老理儿,姐姐怕是没听过,可她清楚圣上午后不接奏报的铁律,便把整盘棋局早早铺开,每一步都算得滴水不漏——连顾天白这个旁观者都暗自咂舌:姐姐这几招落子如风,分明是要把那老学究当场钉死在耻辱柱上。
几日后早朝,本无资格入殿的从四品官、国子杏坛寺祭酒茅南行,竟破例捧著朝笏,天不亮就跪在太和殿外,咬牙切齿要参那个“无法无天”的小姑娘一本。
奏章里字字带刺,说她目中无人、顶撞师长,还顺手把家风拖下水,硬说是家教败坏才养出这般狂悖之徒。
文人的笔尖,比刀锋更冷,比毒药更钝——不见血,却专剜人心。
这事若轻轻揭过,不过私塾里学生呛了先生一句;可若往深里揪,便是踩著天下读书人的脊梁骨走路。
刚登基不久的文胜帝左右为难,既不敢寒了士林的心,又不愿真拿个孩子开刀,乾脆一道旨意甩给大理寺,让专断大案重案的衙门去查这桩鸡毛蒜皮,摆明了向天下秀才示好。
大理寺接了这烫手铜炉,满堂官员直挠头——这等家长里短的腌臢事,还不如提著脑袋去追逃犯来得痛快。
更別提三品大理寺卿,被逼得茶饭不思,连公案上的硃砂印都盖得心不在焉。
老学究焦灼等信儿,大理寺乱作一团,偏生漩涡正中心的姐姐,半点不慌,还笑吟吟教一群娃娃编了首打油诗,天天蹲在大理寺门口齐声吆喝。
第450章 四品大祭酒
正因如此,国子杏坛寺应运而生,成了天下俊彦的匯聚之地。
四书五经、性理算术、诸子百家,处处辩声琅琅;最盛时,连儒教祖庭兗州城外那座千年杏坛,都比不上京城这座新庙里的学风炽烈。
坊间甚至传著一句俏皮话:“杏坛枝头踩断枝,书声压过钟鼓鸣。”
也正因地位超然,歷任大祭酒,无一不是目高於顶的硕儒。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此话不假——建寺五十多年,四任大祭酒,个个傲骨嶙峋,连皇亲国戚登门,也得先递名帖、候通稟。
久而久之,便养出一种惯常的睥睨:仿佛天地间道理,尽在他们袖中卷里。
尤其那位前任大祭酒茅南行,留著一撮山羊鬍,整日鼻孔朝天,走路带风,见谁都像欠他三吊钱。
那天纯属巧合。顾天白素来见书就犯困,平日绕著杏坛寺走,生怕沾上半点墨气。
可那日不知怎的,脚下一拐,竟直奔寺门而去。
仗著在皇城里混了个熟脸,他连腰牌都没掏,就大摇大摆进了这等閒人不得擅入的禁地。
偏巧撞上茅南行——那老头正无所事事,在讲堂间踱著方步。
见他没文书、无引荐,当即沉下脸,厉声呵斥几句,旋即挥手撵人:“哪儿来的野小子?滚出去!”
顾天白本懒得跟这个把律令条文当祖宗牌位供著、拿规矩二字压人喘不过气的老学究多费口舌,抬脚就走。
谁知那老头儿竟追出门外,当场冲守门兵丁横眉竖目,劈头盖脸骂他们失职放进了个“来路不明的野人”。
这倒也罢了——顾天白自觉理亏,毕竟自己仗著几分熟脸,连腰牌都未掏便晃进了这座在西亳百姓眼里堪比宫禁森严的国子杏坛寺。
他心想,这老祭酒多半心里门清:自己虽没官身,但在城里也算掛得上號的人物,人家睁只眼闭只眼,原是给个薄面。
可谁料他刚依言退出杏坛寺大门,那老头儿反倒火上浇油,话里藏针,句句往守卫身上戳,末了竟扬言要递摺子进宫,参这几个门房“瀆职怠慢、不堪任用”,非要摘了他们的差事不可。
顾天白心头一沉,火苗子直往上窜——倒不是怕他告状,而是怕真惹出祸来,让几个老实巴交的兵卒丟了饭碗。
他强压怒意,只上前分辩几句,替那几个被指著鼻子骂的守卫说了两句公道话。就算真被革了职,大不了他亲自去吏部打个招呼,调去城防营或太僕寺做个閒差,总好过在这儿被人当街踩进泥里。
哪知那老祭酒得了势便翻脸不认人,手指几乎戳到顾天白鼻尖,一张嘴全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训斥;
接著又抖著鬍子,咬牙切齿念什么“欲求必达,欲禁必止,欲令必行”,活像背书背岔了气;
更扯出“朽木不可雕”那一套,再配上他那撮被学生暗讽为“牛尾巴毛”的山羊鬍,一边捋一边嘆世风日下,说什么“这般少年蔑法轻律,迟早误国殃民”。
满口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如泼水般倾泻而出——別说那几个只识得刀柄上刻字的守卫听得两眼发直,就连自小被爹娘按在书案前硬灌四书五经的顾天白,听著他那腔调,都差点以为自己偷了太庙香灰、砸了圣旨匣子。
顾天白本打定主意不搭理这尊活规矩碑,偏生那老头儿越说越亢奋,在门口跳脚嚷嚷,活似唱大戏,动静大得连本在街对麵茶楼包间里等他的姐姐都听见了。
旁人或许不知,可姐姐对顾天白那份护短劲儿,早已刻进骨头缝里——四品大祭酒?
她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若真有哪位天子开口挑弟弟半句毛病,这位从小把“护弟即护家”当信条的姐姐,怕是要当场掀了龙椅扶手才肯罢休。
更不用旁人添柴加火。
单瞧那老祭酒指著顾天白破口大骂的模样,活脱脱一个市井泼妇叉腰开骂,连唾沫星子都快溅到弟弟衣领上——姐姐哪里忍得?
三步並作两步上前,脸上还带著平日对祭酒毕恭毕敬的笑意,话却一句比一句扎得准、问得狠:先绕著弯子探他为何发难,再从他话缝里揪出破绽,最后只拎出一条——堂堂国子杏坛寺门前,你一个主官当街咆哮、惊扰学子、搅乱讲学,这算哪门子持重?
老祭酒顿时语塞,手指哆嗦著点了几下,终究憋出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甩袖而去,撂下狠话要去御前告状,非要把这个“目无纲常、胆大妄为”的丫头治个重罪。
可姐姐何曾把这种虚张声势放在眼里?她连眼皮都没抬,只望著那老头儿气冲冲奔向皇城的背影,嘴角微扬,仿佛看的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只扑火的飞蛾。
你以为这事就这么揭过了?
顾天白太了解姐姐——当眾让祭酒顏面扫地,不过是替弟弟挣回一口气;可弟弟被人指著鼻子羞辱,这口气若不一口口討回来,她夜里都睡不踏实。
姐姐回府后即刻动笔列单子,连夜摸清老祭酒平日爱喝什么茶、见客穿哪件袍子、连他书房窗朝哪边开都记在册上;
次日一早,借著给太后送新焙的云雾松针茶之机,混入宫城內院,在冷香亭拐角处“不小心”遗落一只青玉鼻烟壶;
转头又遣心腹去南曲巷头的醉仙楼,请了一位素有才名的校书娘,专挑老祭酒归宅时辰,在他朱漆大门前来回踱步,裙裾轻摆,笑语隱约,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
紧跟著,她命人搜罗齐老祭酒歷年刊印的诗稿、讲义、批註,彻夜未眠,红笔密密圈点,在每页空白处批下犀利评语,字字如刀,句句见血。
这句“先发制人,后发受制”的江湖老理儿,姐姐怕是没听过,可她清楚圣上午后不接奏报的铁律,便把整盘棋局早早铺开,每一步都算得滴水不漏——连顾天白这个旁观者都暗自咂舌:姐姐这几招落子如风,分明是要把那老学究当场钉死在耻辱柱上。
几日后早朝,本无资格入殿的从四品官、国子杏坛寺祭酒茅南行,竟破例捧著朝笏,天不亮就跪在太和殿外,咬牙切齿要参那个“无法无天”的小姑娘一本。
奏章里字字带刺,说她目中无人、顶撞师长,还顺手把家风拖下水,硬说是家教败坏才养出这般狂悖之徒。
文人的笔尖,比刀锋更冷,比毒药更钝——不见血,却专剜人心。
这事若轻轻揭过,不过私塾里学生呛了先生一句;可若往深里揪,便是踩著天下读书人的脊梁骨走路。
刚登基不久的文胜帝左右为难,既不敢寒了士林的心,又不愿真拿个孩子开刀,乾脆一道旨意甩给大理寺,让专断大案重案的衙门去查这桩鸡毛蒜皮,摆明了向天下秀才示好。
大理寺接了这烫手铜炉,满堂官员直挠头——这等家长里短的腌臢事,还不如提著脑袋去追逃犯来得痛快。
更別提三品大理寺卿,被逼得茶饭不思,连公案上的硃砂印都盖得心不在焉。
老学究焦灼等信儿,大理寺乱作一团,偏生漩涡正中心的姐姐,半点不慌,还笑吟吟教一群娃娃编了首打油诗,天天蹲在大理寺门口齐声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