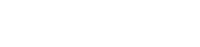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36章 怕我在茶里下毒
约莫一盏茶工夫过去,一道懒洋洋的腔调懒懒飘来:“够了够了,別打了。打死这小杂种,还脏了爷的手。”
那声音乍听寻常,细品却熟悉得扎耳——天白和姐姐同时抬起了头,正是韩有鱼。
幸好天白当时收了力,韩有鱼在床上躺了两三天,灌下几副据说是歷下城首屈一指的老郎中开的汤药,便又生龙活虎起来,旋即被韩鯤鹏硬拽著去了宋家在歷下城的宅子,权当登门谢罪。
递上拜帖,跟宋家在本地坐镇的管事人寒暄敘旧、套近乎,再塞过去几张通宝钱庄全国兑付的银票——明面礼数周全,暗地打点妥帖,这档子麻烦事,就被韩鯤鹏三言两语、四两拨千斤地抹平了。
因上次被那个叫天白的踹得当场昏死,韩有鱼心里发怵,一直缩在杨府不敢出门。偏巧韩鯤鹏又盯得紧,从早到晚寸步不离,这几日简直把他闷得透不过气。
这天,韩有鱼实在憋不住,琢磨著溜出去寻点快活。走正门怕撞上韩鯤鹏,少不得挨一顿囉嗦,便打定主意从后门悄悄摸出去。谁料刚摸到后门,冷不防一道黑影挥刀扑来!
韩有鱼虽在天白手下连一招都没走过,可毕竟练了十几年拳脚,那一脚虽震散了他体內气劲,筋骨力气却没丟。当下脚底一滑,侧身闪开刀锋,稳住身形再细瞧对方步法与架势,立刻断定:不过是个蛮力有余、章法全无的愣头青,拎把劈柴刀就敢闯宅行凶,十足的莽货。眨眼工夫,三拳两腿,那人便仰面栽倒。
闻声赶来的杨家护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將人按牢。韩有鱼抬手一指,家丁们推搡踢打,乾脆利落地把人轰出了杨府大门。
之后的事,便是天白姐弟俩听见的那一出。
外头动静渐息,估摸是韩有鱼带人回去了。天白瞥见姐姐仍僵立原地,一动不动,不用问也知她心里翻腾什么,便放下手中活计,轻声道:“外头风大,你先回屋,我出去瞧瞧。”
姐姐听了,信他从不说虚话,默默转身进了屋。天白隨手拍掉掌心浮灰,在衣襟上胡乱蹭了两下,抬脚朝院外走去。
院外这条道不是主街,窄窄一条,天白刚跨出门槛,就见不远处杨府后门边蜷著个人。月光清冷,照见那人衣衫单薄,只裹一件粗布短褂,在这春寒料峭的夜里早已撕开几道口子,露出底下青紫皮肉;头髮乱如枯草,脸上糊著血污,若非亲眼所见,路上撞见,只当是个饿极了的乞丐。
天白走近,低头俯视——那人仍蜷著,一动不动。待看清面目,才知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眉眼虽被污跡遮掩,一双眼睛却亮得扎眼;肩宽背厚,骨架撑得衣服绷紧,那身板,怕是能把他整个儿兜进怀里。
地上那人察觉有人靠近,原是想缓口气,又喘了几息,才翻身挣扎起身。他看也不看天白一眼,抹一把嘴角血沫,晃晃悠悠便朝前走。
“还好吧?”天白终於开口。
少年充耳不闻,只顾往前挪。
“背上破了,要不要包一下?”那人背影一露,天白才看见肩胛下方裂开一道口子,血珠正慢慢往外渗。
他依旧不吭声。天白甚至疑心,这人要么耳聋,要么哑了。
“吱呀——”
少年刚走过天白姐弟的小院门口,院门忽然推开,姐姐走了出来。可那人脚步未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们姐弟俩不是歹人,只是听见动静才出来看看。”姐姐耳力过人,话音未落已听出他脚步虚浮,顿了顿,又补一句:“你和韩有鱼有仇?”
蛇打七寸,姐姐这话一出,直戳要害。
果然,他脚步猛地钉住。天白清楚看见他双肩微微一颤——仇,怕是深得很。虽说不晓得韩有鱼究竟干了什么,但单看头天他那副嘴脸、那股横劲,十有八九,是欺负了人家闺女或娘亲。
那人脚步一顿,姐姐便接著开口:“就算要报仇,也得先把血止住、伤口包扎妥当吧?我们没半点歹意,屋里烧著炭火,暖和得很,进来歇歇脚,让我弟弟替你上药。我一个瞎子,还能把你怎么著?”
这话温软如絮,偏又透著股篤定,再冷硬的心肠听了,也得鬆动三分。
“天白,快扶他进来!外头风颳得紧,冻僵了皮肉,药都难渗进去。”
话音未落,她已侧身让开门槛,袖角轻扬,姿態从容。
那人却骤然一凛,猛地偏头,乱发后一双眼睛凶光迸射,直直刺向姐姐,嗓音粗糲如砂纸磨过青砖:“你说自己眼盲,又怎知我是男是女?”——这少年,警觉得像只刚离巢的鹰隼。
姐姐却莞尔一笑,先是唇角微翘,继而笑意漫上脸颊,连眼尾都弯成月牙,清亮又舒展。
“我看不见,可耳朵没聋啊。女人喘气是细水长流,柔中带韧;男人哪怕屏息压声,那气息也是沉、是阔、是藏不住的劲道。”她略顿了顿,两道柳叶眉彻底舒展如新月,“眼既瞎了,耳朵,总得练得比常人灵光些。”
屋內,姐姐照旧不慌不忙地煮茶,天白则低头替那少年清理创口。
少年默然不动,天白也缄口不语——从小跟著姐姐习茶,信奉的是“茶烟起时,万语俱寂”。这杯棠茗未尽之前,她绝不开口多话。一时间,炭火噼啪,水沸微响,满室静得能听见呼吸浮沉。
待药粉敷好、布条缠紧,少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窗外朔风卷雪,屋內炭盆烫手,他却只裹著那件千疮百孔的粗麻衣,起身便朝门外走,仿佛这暖意压根儿没沾上他的衣角。
天白暗忖:平日里姐姐煮茶,一步一叩,慢得像数更漏;今日倒似被谁推了一把——关公巡城之后,竟直接暖玉温床,生生跳过三四道工序。
“请留步。”姐姐声音清亮,不疾不徐。
少年果然停步,却不转身,只冷冷拋来一句:“何事?”
“若不急著走,不如坐下来喝盏茶,跟我们姐弟聊聊——你与韩家二少爷,究竟结了多深的梁子?”她边说边撤去旧盏,重洗茶具;天白顺势拨旺炉火,提来井里新汲的凉水,水珠还凝在桶沿。
“他欠我的,轮不到你们插手。”少年口气硬得像块生铁,“今日援手之恩,他日必当厚报。告辞。”说罢朝二人斜抱一拳,动作倒是利落,可那手势顛三倒四——男子作揖,本该左掌覆右拳,他却反其道而行,分明是照猫画虎,徒有其形。
“不愿讲就不讲,可既然踏进这扇门,总得喝完这盏茶。莫非——”她指尖轻叩茶盘,笑意微扬,“怕我在茶里下毒?”
话音未落,她已稳稳接过天白递来的铜壶,手腕轻旋,洗茶、烫盏、淋壶、回汤一气呵成;乌龙入盏,悬壶高冲,水柱如练,茶叶翻涌似浪,真有几分云外飞仙的韵致。
可惜这般曾叫人掷千金只为品一口的绝技,在少年眼里不过是一场冗长拖沓的折腾。
可她最后一句,倒真戳中了他的筋骨:“我薄近侯活到十八岁,还没怕过什么。”话音未落,已大剌剌往姐姐对面一坐,袍角扫过竹蓆,毫不客气。
第436章 怕我在茶里下毒
约莫一盏茶工夫过去,一道懒洋洋的腔调懒懒飘来:“够了够了,別打了。打死这小杂种,还脏了爷的手。”
那声音乍听寻常,细品却熟悉得扎耳——天白和姐姐同时抬起了头,正是韩有鱼。
幸好天白当时收了力,韩有鱼在床上躺了两三天,灌下几副据说是歷下城首屈一指的老郎中开的汤药,便又生龙活虎起来,旋即被韩鯤鹏硬拽著去了宋家在歷下城的宅子,权当登门谢罪。
递上拜帖,跟宋家在本地坐镇的管事人寒暄敘旧、套近乎,再塞过去几张通宝钱庄全国兑付的银票——明面礼数周全,暗地打点妥帖,这档子麻烦事,就被韩鯤鹏三言两语、四两拨千斤地抹平了。
因上次被那个叫天白的踹得当场昏死,韩有鱼心里发怵,一直缩在杨府不敢出门。偏巧韩鯤鹏又盯得紧,从早到晚寸步不离,这几日简直把他闷得透不过气。
这天,韩有鱼实在憋不住,琢磨著溜出去寻点快活。走正门怕撞上韩鯤鹏,少不得挨一顿囉嗦,便打定主意从后门悄悄摸出去。谁料刚摸到后门,冷不防一道黑影挥刀扑来!
韩有鱼虽在天白手下连一招都没走过,可毕竟练了十几年拳脚,那一脚虽震散了他体內气劲,筋骨力气却没丟。当下脚底一滑,侧身闪开刀锋,稳住身形再细瞧对方步法与架势,立刻断定:不过是个蛮力有余、章法全无的愣头青,拎把劈柴刀就敢闯宅行凶,十足的莽货。眨眼工夫,三拳两腿,那人便仰面栽倒。
闻声赶来的杨家护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將人按牢。韩有鱼抬手一指,家丁们推搡踢打,乾脆利落地把人轰出了杨府大门。
之后的事,便是天白姐弟俩听见的那一出。
外头动静渐息,估摸是韩有鱼带人回去了。天白瞥见姐姐仍僵立原地,一动不动,不用问也知她心里翻腾什么,便放下手中活计,轻声道:“外头风大,你先回屋,我出去瞧瞧。”
姐姐听了,信他从不说虚话,默默转身进了屋。天白隨手拍掉掌心浮灰,在衣襟上胡乱蹭了两下,抬脚朝院外走去。
院外这条道不是主街,窄窄一条,天白刚跨出门槛,就见不远处杨府后门边蜷著个人。月光清冷,照见那人衣衫单薄,只裹一件粗布短褂,在这春寒料峭的夜里早已撕开几道口子,露出底下青紫皮肉;头髮乱如枯草,脸上糊著血污,若非亲眼所见,路上撞见,只当是个饿极了的乞丐。
天白走近,低头俯视——那人仍蜷著,一动不动。待看清面目,才知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眉眼虽被污跡遮掩,一双眼睛却亮得扎眼;肩宽背厚,骨架撑得衣服绷紧,那身板,怕是能把他整个儿兜进怀里。
地上那人察觉有人靠近,原是想缓口气,又喘了几息,才翻身挣扎起身。他看也不看天白一眼,抹一把嘴角血沫,晃晃悠悠便朝前走。
“还好吧?”天白终於开口。
少年充耳不闻,只顾往前挪。
“背上破了,要不要包一下?”那人背影一露,天白才看见肩胛下方裂开一道口子,血珠正慢慢往外渗。
他依旧不吭声。天白甚至疑心,这人要么耳聋,要么哑了。
“吱呀——”
少年刚走过天白姐弟的小院门口,院门忽然推开,姐姐走了出来。可那人脚步未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们姐弟俩不是歹人,只是听见动静才出来看看。”姐姐耳力过人,话音未落已听出他脚步虚浮,顿了顿,又补一句:“你和韩有鱼有仇?”
蛇打七寸,姐姐这话一出,直戳要害。
果然,他脚步猛地钉住。天白清楚看见他双肩微微一颤——仇,怕是深得很。虽说不晓得韩有鱼究竟干了什么,但单看头天他那副嘴脸、那股横劲,十有八九,是欺负了人家闺女或娘亲。
那人脚步一顿,姐姐便接著开口:“就算要报仇,也得先把血止住、伤口包扎妥当吧?我们没半点歹意,屋里烧著炭火,暖和得很,进来歇歇脚,让我弟弟替你上药。我一个瞎子,还能把你怎么著?”
这话温软如絮,偏又透著股篤定,再冷硬的心肠听了,也得鬆动三分。
“天白,快扶他进来!外头风颳得紧,冻僵了皮肉,药都难渗进去。”
话音未落,她已侧身让开门槛,袖角轻扬,姿態从容。
那人却骤然一凛,猛地偏头,乱发后一双眼睛凶光迸射,直直刺向姐姐,嗓音粗糲如砂纸磨过青砖:“你说自己眼盲,又怎知我是男是女?”——这少年,警觉得像只刚离巢的鹰隼。
姐姐却莞尔一笑,先是唇角微翘,继而笑意漫上脸颊,连眼尾都弯成月牙,清亮又舒展。
“我看不见,可耳朵没聋啊。女人喘气是细水长流,柔中带韧;男人哪怕屏息压声,那气息也是沉、是阔、是藏不住的劲道。”她略顿了顿,两道柳叶眉彻底舒展如新月,“眼既瞎了,耳朵,总得练得比常人灵光些。”
屋內,姐姐照旧不慌不忙地煮茶,天白则低头替那少年清理创口。
少年默然不动,天白也缄口不语——从小跟著姐姐习茶,信奉的是“茶烟起时,万语俱寂”。这杯棠茗未尽之前,她绝不开口多话。一时间,炭火噼啪,水沸微响,满室静得能听见呼吸浮沉。
待药粉敷好、布条缠紧,少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窗外朔风卷雪,屋內炭盆烫手,他却只裹著那件千疮百孔的粗麻衣,起身便朝门外走,仿佛这暖意压根儿没沾上他的衣角。
天白暗忖:平日里姐姐煮茶,一步一叩,慢得像数更漏;今日倒似被谁推了一把——关公巡城之后,竟直接暖玉温床,生生跳过三四道工序。
“请留步。”姐姐声音清亮,不疾不徐。
少年果然停步,却不转身,只冷冷拋来一句:“何事?”
“若不急著走,不如坐下来喝盏茶,跟我们姐弟聊聊——你与韩家二少爷,究竟结了多深的梁子?”她边说边撤去旧盏,重洗茶具;天白顺势拨旺炉火,提来井里新汲的凉水,水珠还凝在桶沿。
“他欠我的,轮不到你们插手。”少年口气硬得像块生铁,“今日援手之恩,他日必当厚报。告辞。”说罢朝二人斜抱一拳,动作倒是利落,可那手势顛三倒四——男子作揖,本该左掌覆右拳,他却反其道而行,分明是照猫画虎,徒有其形。
“不愿讲就不讲,可既然踏进这扇门,总得喝完这盏茶。莫非——”她指尖轻叩茶盘,笑意微扬,“怕我在茶里下毒?”
话音未落,她已稳稳接过天白递来的铜壶,手腕轻旋,洗茶、烫盏、淋壶、回汤一气呵成;乌龙入盏,悬壶高冲,水柱如练,茶叶翻涌似浪,真有几分云外飞仙的韵致。
可惜这般曾叫人掷千金只为品一口的绝技,在少年眼里不过是一场冗长拖沓的折腾。
可她最后一句,倒真戳中了他的筋骨:“我薄近侯活到十八岁,还没怕过什么。”话音未落,已大剌剌往姐姐对面一坐,袍角扫过竹蓆,毫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