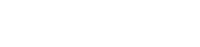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37章 图的就是个痛快
天白心头微哂:这人,算是被姐姐拿捏得死死的——果然是胳膊粗的,心眼儿就细不了。
这位自称薄近侯的少年面朝天白而坐,脸上糊著泥灰油垢,辨不清本来面目,唯有一双眼睛亮得灼人;只是那副懒散倚靠的姿態,生生把这点神采也压下去几分。
“倒茶!”他朝姐姐朗声一唤,嗓门敞亮,毫无扭捏,倒让天白心里又添了三分好感。
姐姐浅笑,素手一挽云袖,语气轻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特意说给他听:“喝茶,贵在心平气和——太急,茶涩;太慢,香散。
烧水也有讲究:鱼眼初泛,蟹眼將生,火候正在此处。悬壶高冲,是为撞开蜷缩的叶脉,逼出沉睡的魂香。
斟茶须守礼:先巡城,再点兵,人人有份,一个不落。敬茶更有章法:三指托盏如龙护鼎,倾身奉客似昭君出塞。”
嘴上说著,手上不停,动作利落得让薄近侯直眨巴眼。若非那双眸子空茫茫没半点光亮,他死也不信眼前这瞎姑娘竟能稳稳將水注进壶嘴、再一滴不洒地斟满茶盏——待那杯茶递到跟前,薄近侯还傻愣著,眼珠子都忘了转。
请用茶。
一声轻唤,才把他魂儿拽回来。他略带窘意地接过那只街边茶摊最寻常不过的青釉盖碗,仰头就是一大口,喉结滚动,喝得乾脆又敞亮。
爽快!
姐姐笑著赞了一句,隨即摇头道:“本该是大碗筛酒、大块嚼肉的性子,偏来喝这费时辰的淡茶,倒像拿绣花针缝大袄,活生生糟蹋了人。”
可不是嘛!人活一世,图的就是个痛快!喝口酒磨磨唧唧,扭扭捏捏跟个小媳妇似的,浑身不得劲儿!
薄近侯故作老成,啪地一拍桌子,倒真有几分一见如故的热络。
可话音刚落,脑中忽然一闪——对面这位姑娘方才不就干了他嘴里那个“不得劲儿”的活计么?一时语塞,后半截话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姐姐却像压根没听见他这句莽撞话,反倒拊掌一笑:“好一个『人活在世痛快二字』!光凭这八个字,就该浮一大白!”说完,扭头望向旁边正暗自咋舌的天白——这少年才说了几句话,竟把那毛头小子哄得眉开眼笑,实在叫人佩服——又道:“去,把酒拿来,今儿得好好碰几碗。”
薄近侯咧嘴憨笑,本就亮堂的眼睛此刻灼灼生光,活像饿狼盯上了鲜肉。
天白心底一嘆:姐姐虽目不能视,可这份拿捏人心的火候,旁人真难望其项背。
姐姐的酒量,打小就隨了那位酒罈子里泡大的爹。
甭管是市井巷尾人人喝得起的洛神浆,还是只在京城里琉璃瓦、碧檐牙底下才摆得上桌的蓬莱酿,天白记事起,就没见她醉过一回。
端上来的自然是 的洛神浆,没菜没碟,三人就捧著盖碗对饮。薄近侯来者不拒,一碗接一碗,天白心里那点戒备,也跟著酒气散了几分。
小兄弟可晓得,为啥这洛神浆,偏偏是咱们大周最便宜的酒?
姐姐像是隨口一问,实则话里有鉤。
这酒看著平平无奇,劲头却不软——连干三碗,常人早该脸红耳热、舌头打结。
可薄近侯呼吸匀长,气息稳当,显见是条能扛得住的硬汉。
我打小就知道它便宜,你要问我为啥便宜……还真答不上来。薄近侯酒意微醺,防备心也鬆了扣子。
酒这东西就是怪,再生疏的人,几碗下肚,便熟得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我平时就蹭他们剩的酒喝,什么贵贱好坏,哪分得清?只觉解渴,解馋,够劲儿就行。
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了——这才半炷香工夫,他已从绷著脸的刺蝟,变成敞著心窝子的傻小子。
这说话的功夫,天白真是服了。
酒麴用的是关中头茬麦子,蒸酒烧的是洛河水。
关中沃土,尤其洛河两岸,风调雨顺,麦子一年两熟;再掺些包芦入缸发酵。
酿酒的手法也透著关中人的脾性——敞开发酵、烈火蒸馏,粗獷豪迈。
所以酒香清淡,后劲却沉,一口下去,温润是假象,灼烧才是真章。
省工省料,价自然就低了。
姐姐语气平缓,几句话就把洛神浆的筋骨讲得清清楚楚。薄近侯听得发怔,差点疑心她从前就是蹲在酒坊里踩曲的老匠人。
我就是个糙胚,这些弯弯绕绕,听不懂,也不想懂。
薄近侯一把抓过天白刚满上的酒碗,仰脖灌尽,长长呼出一口白气。
低头时眼尾泛红,泪光一闪而没,旋即又伸手抄起酒壶,哗啦啦倒满,咕嘟一声咽下去,仿佛要把那点湿意也一併压进肚里。
什么喝茶喝酒,在我们这种人眼里,就得这么喝——解渴,解馋,解一口气!
话音未落,又是一碗见底。
六碗下肚,薄近侯麵皮泛起潮红,可那双眼睛却越发明亮,映著灯焰,像两簇不肯熄的火苗。
小兄弟不是也说,人活一世,图个痛快?怎么眼下,倒缩手缩脚,小气起来了?
姐姐伸手探向酒壶,循著方才碗沿磕在桌上的脆响,准確摸到位置,稳稳给他添满,声音温软却不容推拒:喝酒,就得痛快著喝。若借酒浇愁,愁没浇灭,酒气先烧穿了脑子——那才叫真糟心。
薄近侯被姐姐这话戳中了心口,喉头一紧,半晌没吭声。姐姐却不动声色,只把话头往深里引。
“人活这一遭,十桩事里九桩不顺心,翻篇就翻篇吧。你今儿夜里寻韩有鱼去,图个什么?真能討回公道?
怕是连门都没摸进,反倒挨了一顿狠揍——茶凉了三巡,味儿就散了;
咱们这壶洛神浆再烈,醉过一场,天亮睁眼,也就醒了。
冤冤相报,哪有个尽头?你跟韩有鱼本就不是同道中人,硬撞上去,落得什么下场?不过皮肉受苦,自己咽下这口闷气罢了。”
她说话间似渴得厉害,端起盖碗仰脖灌了一口酒,酒液滑入喉咙,才又缓缓道:“多大的恨,非要拼到这份上?”
“你懂什么!”薄近侯猛地拍桌,震得碗碟乱跳,声音炸雷似的劈开屋里的沉闷。他牙关咬得死紧,额角青筋直跳,连旁边自斟自饮的天白都惊得手一抖,酒洒了半袖。
换作往日,姐姐被人这般顶撞,天白早按捺不住要起身拦话。可今夜他只是垂著眼,脚尖在桌下轻轻碰了碰姐姐的鞋面,像是提醒,又像安抚。
“难不成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姐姐这话刚落,火候便到了。
薄近侯右拳攥得咯咯作响,指节泛白,仿佛要把满口牙齿生生咬碎,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字字带血:“比杀父更甚!”
话音未落,他仰头干尽一碗酒,低头时泪已滚落,却死死咬住下唇不许自己哽咽出声:“他杀了我姨娘。”
他又自斟满碗,双眼赤红,將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倒了出来。
薄近侯十八岁,祖籍南疆。早年家中也算富庶,三代经商,银钱厚实。
偏生到他父亲这一辈,家业如沙塔崩塌。
他五岁那年,父亲押上全部家当与人合伙做绸缎生意,谁料对方捲款潜逃,本金利钱一併吞尽,还欠下几百两外债。
变卖田產铺面,也只填上一半窟窿。
债主日日堵门,父亲急火攻心,中风倒地,一口气没接上来,撒手而去。
孤儿寡母哪还有力气扛这山样债务?债主翻脸无情,一纸诉状告上衙门。
按大周律,无力偿债者,依欠款多少判为奴籍。
薄家欠得太多,一家老小尽数发卖,才堪堪抹平帐目。
第437章 图的就是个痛快
天白心头微哂:这人,算是被姐姐拿捏得死死的——果然是胳膊粗的,心眼儿就细不了。
这位自称薄近侯的少年面朝天白而坐,脸上糊著泥灰油垢,辨不清本来面目,唯有一双眼睛亮得灼人;只是那副懒散倚靠的姿態,生生把这点神采也压下去几分。
“倒茶!”他朝姐姐朗声一唤,嗓门敞亮,毫无扭捏,倒让天白心里又添了三分好感。
姐姐浅笑,素手一挽云袖,语气轻缓,像是自言自语,又像特意说给他听:“喝茶,贵在心平气和——太急,茶涩;太慢,香散。
烧水也有讲究:鱼眼初泛,蟹眼將生,火候正在此处。悬壶高冲,是为撞开蜷缩的叶脉,逼出沉睡的魂香。
斟茶须守礼:先巡城,再点兵,人人有份,一个不落。敬茶更有章法:三指托盏如龙护鼎,倾身奉客似昭君出塞。”
嘴上说著,手上不停,动作利落得让薄近侯直眨巴眼。若非那双眸子空茫茫没半点光亮,他死也不信眼前这瞎姑娘竟能稳稳將水注进壶嘴、再一滴不洒地斟满茶盏——待那杯茶递到跟前,薄近侯还傻愣著,眼珠子都忘了转。
请用茶。
一声轻唤,才把他魂儿拽回来。他略带窘意地接过那只街边茶摊最寻常不过的青釉盖碗,仰头就是一大口,喉结滚动,喝得乾脆又敞亮。
爽快!
姐姐笑著赞了一句,隨即摇头道:“本该是大碗筛酒、大块嚼肉的性子,偏来喝这费时辰的淡茶,倒像拿绣花针缝大袄,活生生糟蹋了人。”
可不是嘛!人活一世,图的就是个痛快!喝口酒磨磨唧唧,扭扭捏捏跟个小媳妇似的,浑身不得劲儿!
薄近侯故作老成,啪地一拍桌子,倒真有几分一见如故的热络。
可话音刚落,脑中忽然一闪——对面这位姑娘方才不就干了他嘴里那个“不得劲儿”的活计么?一时语塞,后半截话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
姐姐却像压根没听见他这句莽撞话,反倒拊掌一笑:“好一个『人活在世痛快二字』!光凭这八个字,就该浮一大白!”说完,扭头望向旁边正暗自咋舌的天白——这少年才说了几句话,竟把那毛头小子哄得眉开眼笑,实在叫人佩服——又道:“去,把酒拿来,今儿得好好碰几碗。”
薄近侯咧嘴憨笑,本就亮堂的眼睛此刻灼灼生光,活像饿狼盯上了鲜肉。
天白心底一嘆:姐姐虽目不能视,可这份拿捏人心的火候,旁人真难望其项背。
姐姐的酒量,打小就隨了那位酒罈子里泡大的爹。
甭管是市井巷尾人人喝得起的洛神浆,还是只在京城里琉璃瓦、碧檐牙底下才摆得上桌的蓬莱酿,天白记事起,就没见她醉过一回。
端上来的自然是 的洛神浆,没菜没碟,三人就捧著盖碗对饮。薄近侯来者不拒,一碗接一碗,天白心里那点戒备,也跟著酒气散了几分。
小兄弟可晓得,为啥这洛神浆,偏偏是咱们大周最便宜的酒?
姐姐像是隨口一问,实则话里有鉤。
这酒看著平平无奇,劲头却不软——连干三碗,常人早该脸红耳热、舌头打结。
可薄近侯呼吸匀长,气息稳当,显见是条能扛得住的硬汉。
我打小就知道它便宜,你要问我为啥便宜……还真答不上来。薄近侯酒意微醺,防备心也鬆了扣子。
酒这东西就是怪,再生疏的人,几碗下肚,便熟得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我平时就蹭他们剩的酒喝,什么贵贱好坏,哪分得清?只觉解渴,解馋,够劲儿就行。
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了——这才半炷香工夫,他已从绷著脸的刺蝟,变成敞著心窝子的傻小子。
这说话的功夫,天白真是服了。
酒麴用的是关中头茬麦子,蒸酒烧的是洛河水。
关中沃土,尤其洛河两岸,风调雨顺,麦子一年两熟;再掺些包芦入缸发酵。
酿酒的手法也透著关中人的脾性——敞开发酵、烈火蒸馏,粗獷豪迈。
所以酒香清淡,后劲却沉,一口下去,温润是假象,灼烧才是真章。
省工省料,价自然就低了。
姐姐语气平缓,几句话就把洛神浆的筋骨讲得清清楚楚。薄近侯听得发怔,差点疑心她从前就是蹲在酒坊里踩曲的老匠人。
我就是个糙胚,这些弯弯绕绕,听不懂,也不想懂。
薄近侯一把抓过天白刚满上的酒碗,仰脖灌尽,长长呼出一口白气。
低头时眼尾泛红,泪光一闪而没,旋即又伸手抄起酒壶,哗啦啦倒满,咕嘟一声咽下去,仿佛要把那点湿意也一併压进肚里。
什么喝茶喝酒,在我们这种人眼里,就得这么喝——解渴,解馋,解一口气!
话音未落,又是一碗见底。
六碗下肚,薄近侯麵皮泛起潮红,可那双眼睛却越发明亮,映著灯焰,像两簇不肯熄的火苗。
小兄弟不是也说,人活一世,图个痛快?怎么眼下,倒缩手缩脚,小气起来了?
姐姐伸手探向酒壶,循著方才碗沿磕在桌上的脆响,准確摸到位置,稳稳给他添满,声音温软却不容推拒:喝酒,就得痛快著喝。若借酒浇愁,愁没浇灭,酒气先烧穿了脑子——那才叫真糟心。
薄近侯被姐姐这话戳中了心口,喉头一紧,半晌没吭声。姐姐却不动声色,只把话头往深里引。
“人活这一遭,十桩事里九桩不顺心,翻篇就翻篇吧。你今儿夜里寻韩有鱼去,图个什么?真能討回公道?
怕是连门都没摸进,反倒挨了一顿狠揍——茶凉了三巡,味儿就散了;
咱们这壶洛神浆再烈,醉过一场,天亮睁眼,也就醒了。
冤冤相报,哪有个尽头?你跟韩有鱼本就不是同道中人,硬撞上去,落得什么下场?不过皮肉受苦,自己咽下这口闷气罢了。”
她说话间似渴得厉害,端起盖碗仰脖灌了一口酒,酒液滑入喉咙,才又缓缓道:“多大的恨,非要拼到这份上?”
“你懂什么!”薄近侯猛地拍桌,震得碗碟乱跳,声音炸雷似的劈开屋里的沉闷。他牙关咬得死紧,额角青筋直跳,连旁边自斟自饮的天白都惊得手一抖,酒洒了半袖。
换作往日,姐姐被人这般顶撞,天白早按捺不住要起身拦话。可今夜他只是垂著眼,脚尖在桌下轻轻碰了碰姐姐的鞋面,像是提醒,又像安抚。
“难不成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姐姐这话刚落,火候便到了。
薄近侯右拳攥得咯咯作响,指节泛白,仿佛要把满口牙齿生生咬碎,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字字带血:“比杀父更甚!”
话音未落,他仰头干尽一碗酒,低头时泪已滚落,却死死咬住下唇不许自己哽咽出声:“他杀了我姨娘。”
他又自斟满碗,双眼赤红,將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倒了出来。
薄近侯十八岁,祖籍南疆。早年家中也算富庶,三代经商,银钱厚实。
偏生到他父亲这一辈,家业如沙塔崩塌。
他五岁那年,父亲押上全部家当与人合伙做绸缎生意,谁料对方捲款潜逃,本金利钱一併吞尽,还欠下几百两外债。
变卖田產铺面,也只填上一半窟窿。
债主日日堵门,父亲急火攻心,中风倒地,一口气没接上来,撒手而去。
孤儿寡母哪还有力气扛这山样债务?债主翻脸无情,一纸诉状告上衙门。
按大周律,无力偿债者,依欠款多少判为奴籍。
薄家欠得太多,一家老小尽数发卖,才堪堪抹平帐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