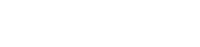齐国到底还是没扛住。
秦军的攻势太猛,那些经过“神水”强化的兵士根本不是普通军队能抵挡的,加上偶尔出现的、会施展诡异手段的“修士”,齐国的防线一溃千里。
没等另外三国反应过来,齐王的车驾就出了临淄城,白衣素服,捧著印璽和图册,向秦军主帅投降了。
消息传回咸阳,贏乐只是淡淡一笑,继续著他那日渐精深的修为。
对於投降的齐王,他懒得见面,直接下旨將其软禁在咸阳一处宅邸。至於齐国献上的所谓“和亲”公主,他更没兴趣。
“公主?”
贏乐嗤笑一声,对身边侍奉的宦官说,
“亡国之女,也配称公主?打发去掖庭,学学规矩,当个宫女吧。”
一句话,就定了那女子的命运。
齐国公主,名叫玉漱。原本在齐国也是金枝玉叶,精通诗书音律,容顏清丽脱俗。
一夜之间,国破家亡,被当成一件求和的政治礼物送入虎狼之秦,却连秦王的面都没见到,就直接从云端跌落,成了这深宫里最低等的宫女。
她被分到了织造处,每天有纺不完的线,织不完的布。纤细的手指很快被粗糙的纺锤和丝线磨出了水泡,又变成厚茧。
娇嫩的皮肤受不了咸阳乾燥寒冷的气候,开始开裂。吃的也是最粗劣的食物,住的是几十人挤在一起的潮湿大通铺。
身份落差,亡国的悲痛,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这陌生环境的极度不適应,几乎將她击垮。
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白天则像个木偶一样,麻木地干活,眼神空洞,很少说话。
她不懂秦宫的规矩,动作稍慢或出错,就会招来管事嬤嬤的打骂和同伴的排挤。
“看什么看?还以为自己是公主呢?”
“快点干!装什么娇弱!”
“齐国的女人就是没用!”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
她越发的沉默和畏缩,像一朵迅速枯萎的。
易小川如今已不是那个永巷刷马桶的小太监了。
凭著钻营和胸口那虎形玉佩带来的力量改变,他混到了內务府下属的一个採买小管事的位置,虽然品级不高,但偶尔能在外廷走动,也能接触到一些宫內物资的分派,手里有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力。
一天,他去织造处送一批新到的染料清单。
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个管事的凶悍老嬤嬤,正指著一个小宫女的鼻子厉声斥骂,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对方脸上了。
“笨手笨脚!这么点丝线都理不好!还敢顶嘴?今天完不成任务,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那小宫女低著头,肩膀微微颤抖,咬著嘴唇,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有掉下来,也没有求饶。
只是,那单薄的身影,在初冬的冷风里,显得格外可怜。
易小川本来懒得管这种閒事,宫里欺负人的事儿多了去了。
他正准备绕开,目光无意中扫过那宫女的脸。
却见那女子:
容顏如初雪映月,清冷中透著一丝柔光。
眉如远山含黛,眼若秋水凝波,让人心尖微颤。
唇瓣轻抿时似瓣含露,叫人移不开视线。
那一刻,仿佛世间喧囂皆止,唯余她眸中流转的星辰,让人甘愿沉溺。
即使穿著粗布衣裳,即使脸色苍白,即使眼角带著泪光,也美得让人心惊。
易小川愣在原地。
他来秦朝这么久,见惯了麻木、諂媚、凶狠、算计的面孔,自己也都快变成那样的人了。
可眼前这张脸,一下子把他拉回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他还相信爱情、相信美好的现代世界。
这感觉太陌生,又太强烈。
那老嬤嬤看见易小川,立刻换上一副笑脸:
“哎呦,川管事,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丫头笨得很,我正在教她规矩呢。”
说著又要去掐那宫女。
易小川鬼使神差地开口了:
“张嬤嬤,火气別这么大。小姑娘家,慢慢教就是了。”
张嬤嬤一愣,没想到这小管事会为个底层宫女说话,但看他脸色如常,也不好多说,只得赔笑:
“是是是,川管事说的是。”
易小川把清单交给张嬤嬤,眼睛却又瞟向那宫女。她似乎也感受到有人帮她,悄悄抬起眼看了他一下,那眼神里的感激,让易小川心里又是一颤。
他状若无意地问:“这丫头看著面生,新来的?”
“可不是嘛,就是前几天齐国献过来的那个什么……亡国公主。”
张嬤嬤语气带著不屑,
“屁用没有,就会添乱。”
齐国公主?易小川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是她。他压下心头的波澜,点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但从那天起,玉漱的影子就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了。
他那颗在阴谋和屈辱中变得冷硬的心,好像裂开了一条缝,照进了一点光。
他知道这很危险,在宫里对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身份敏感的女人动心思,是取死之道。
但他控制不住。
他开始利用那点小小的职权,暗中照顾她。
他去织造处的次数莫名多了起来。有时是“检查物料”,有时是“传达指令”。每次去,都会留意玉漱的情况。
他看到玉漱手上的伤,下次再来时,会“恰好”多带了一小罐效果不错的廉价伤药,隨手递给张嬤嬤:
“上次宫里赏的,我用不著,给她们分分,手粗了怎么干活?”
眼睛却看著玉漱的方向。
他看到玉漱份例里的食物被剋扣得厉害,下次分配物资时,会“疏忽”地多给织造处一点点耐放的饼饵,或者故意把一批稍微好点的粟米“错”分到她们那里。
他偶尔会“路过”织造处后院,看到玉漱一个人偷偷抹眼泪,他会故意弄出点声响,等她惊慌地擦乾眼泪看过来时,他又已经走远,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玉漱一开始並没注意到这个偶尔出现的年轻太监。但次数多了,她隱隱感觉到有些不一样。
手上的药膏,偶尔能分到多一点的食物,那个在她最无助时帮她解围的身影……她不確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心里存了一份疑惑和微弱的感激。
一次,玉漱被派去给一处偏僻宫室送洗好的衣物。回来时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冷雨,她迷路了,又冷又怕,缩在一个廊檐下发抖。
易小川刚好办完差事回来,远远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心里一紧,快步走过去。
“怎么在这儿?”
他开口,也儘量温柔。
玉漱嚇了一跳,抬头看见是他,认出是那个帮过她的管事太监,心里稍安,但又立刻低下头,小声道:
“迷……迷路了……”
雨打湿了她的头髮和单薄的衣衫,冷得她嘴唇发紫,身子微微发抖,看起来可怜极了。
易小川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
他看了看四周,迅速脱下自己那件还算厚实的外衫,不由分说地披在她身上。
“穿上,跟我走。”
他的语气带著命令,玉漱从没没感受过的霸道。
玉漱愣住了,感受著带著陌生男子体温的衣衫,脸颊莫名一热,心跳得快了些。
“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冻死在这里?”
易小川打断她,声音压得很低,“不想惹麻烦就快点。”
他率先走在前面,步伐不快,確保她能跟上。七拐八绕,很快就把她带回了织造处附近。
“前面就到了,你自己进去。”
易小川停下脚步,接过她递还的、已经半湿的外衫,低声快速说,
“以后机灵点,认认路。”
玉漱看著他被雨打湿的侧脸,心里百感交集,鼓起勇气问:
“你……你为什么帮我?”
易小川身体僵了一下,没有看她,只是望著远处的雨幕,沉默了片刻,才含糊地说:
“宫里活著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快步消失在雨夜里。
玉漱站在原地,看著他消失的方向,心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这个沉默寡言、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太监,成了她在这冰冷深宫里,唯一一点模糊的依靠。
而易小川,走在回去的路上,冷雨打在他脸上,心里却一片滚烫。他知道自己不该这样,这很危险。
但那种暗中守护一个人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变回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只知道往上爬的怪物。
他摸了摸胸口那虎形烙印,眼神复杂。
“玉漱……”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一遍又一遍。
秦军的攻势太猛,那些经过“神水”强化的兵士根本不是普通军队能抵挡的,加上偶尔出现的、会施展诡异手段的“修士”,齐国的防线一溃千里。
没等另外三国反应过来,齐王的车驾就出了临淄城,白衣素服,捧著印璽和图册,向秦军主帅投降了。
消息传回咸阳,贏乐只是淡淡一笑,继续著他那日渐精深的修为。
对於投降的齐王,他懒得见面,直接下旨將其软禁在咸阳一处宅邸。至於齐国献上的所谓“和亲”公主,他更没兴趣。
“公主?”
贏乐嗤笑一声,对身边侍奉的宦官说,
“亡国之女,也配称公主?打发去掖庭,学学规矩,当个宫女吧。”
一句话,就定了那女子的命运。
齐国公主,名叫玉漱。原本在齐国也是金枝玉叶,精通诗书音律,容顏清丽脱俗。
一夜之间,国破家亡,被当成一件求和的政治礼物送入虎狼之秦,却连秦王的面都没见到,就直接从云端跌落,成了这深宫里最低等的宫女。
她被分到了织造处,每天有纺不完的线,织不完的布。纤细的手指很快被粗糙的纺锤和丝线磨出了水泡,又变成厚茧。
娇嫩的皮肤受不了咸阳乾燥寒冷的气候,开始开裂。吃的也是最粗劣的食物,住的是几十人挤在一起的潮湿大通铺。
身份落差,亡国的悲痛,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这陌生环境的极度不適应,几乎將她击垮。
她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白天则像个木偶一样,麻木地干活,眼神空洞,很少说话。
她不懂秦宫的规矩,动作稍慢或出错,就会招来管事嬤嬤的打骂和同伴的排挤。
“看什么看?还以为自己是公主呢?”
“快点干!装什么娇弱!”
“齐国的女人就是没用!”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她心上。
她越发的沉默和畏缩,像一朵迅速枯萎的。
易小川如今已不是那个永巷刷马桶的小太监了。
凭著钻营和胸口那虎形玉佩带来的力量改变,他混到了內务府下属的一个採买小管事的位置,虽然品级不高,但偶尔能在外廷走动,也能接触到一些宫內物资的分派,手里有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力。
一天,他去织造处送一批新到的染料清单。
刚进院子,就看见一个管事的凶悍老嬤嬤,正指著一个小宫女的鼻子厉声斥骂,唾沫星子都快喷到对方脸上了。
“笨手笨脚!这么点丝线都理不好!还敢顶嘴?今天完不成任务,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那小宫女低著头,肩膀微微颤抖,咬著嘴唇,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有掉下来,也没有求饶。
只是,那单薄的身影,在初冬的冷风里,显得格外可怜。
易小川本来懒得管这种閒事,宫里欺负人的事儿多了去了。
他正准备绕开,目光无意中扫过那宫女的脸。
却见那女子:
容顏如初雪映月,清冷中透著一丝柔光。
眉如远山含黛,眼若秋水凝波,让人心尖微颤。
唇瓣轻抿时似瓣含露,叫人移不开视线。
那一刻,仿佛世间喧囂皆止,唯余她眸中流转的星辰,让人甘愿沉溺。
即使穿著粗布衣裳,即使脸色苍白,即使眼角带著泪光,也美得让人心惊。
易小川愣在原地。
他来秦朝这么久,见惯了麻木、諂媚、凶狠、算计的面孔,自己也都快变成那样的人了。
可眼前这张脸,一下子把他拉回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他还相信爱情、相信美好的现代世界。
这感觉太陌生,又太强烈。
那老嬤嬤看见易小川,立刻换上一副笑脸:
“哎呦,川管事,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丫头笨得很,我正在教她规矩呢。”
说著又要去掐那宫女。
易小川鬼使神差地开口了:
“张嬤嬤,火气別这么大。小姑娘家,慢慢教就是了。”
张嬤嬤一愣,没想到这小管事会为个底层宫女说话,但看他脸色如常,也不好多说,只得赔笑:
“是是是,川管事说的是。”
易小川把清单交给张嬤嬤,眼睛却又瞟向那宫女。她似乎也感受到有人帮她,悄悄抬起眼看了他一下,那眼神里的感激,让易小川心里又是一颤。
他状若无意地问:“这丫头看著面生,新来的?”
“可不是嘛,就是前几天齐国献过来的那个什么……亡国公主。”
张嬤嬤语气带著不屑,
“屁用没有,就会添乱。”
齐国公主?易小川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是她。他压下心头的波澜,点点头,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但从那天起,玉漱的影子就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了。
他那颗在阴谋和屈辱中变得冷硬的心,好像裂开了一条缝,照进了一点光。
他知道这很危险,在宫里对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身份敏感的女人动心思,是取死之道。
但他控制不住。
他开始利用那点小小的职权,暗中照顾她。
他去织造处的次数莫名多了起来。有时是“检查物料”,有时是“传达指令”。每次去,都会留意玉漱的情况。
他看到玉漱手上的伤,下次再来时,会“恰好”多带了一小罐效果不错的廉价伤药,隨手递给张嬤嬤:
“上次宫里赏的,我用不著,给她们分分,手粗了怎么干活?”
眼睛却看著玉漱的方向。
他看到玉漱份例里的食物被剋扣得厉害,下次分配物资时,会“疏忽”地多给织造处一点点耐放的饼饵,或者故意把一批稍微好点的粟米“错”分到她们那里。
他偶尔会“路过”织造处后院,看到玉漱一个人偷偷抹眼泪,他会故意弄出点声响,等她惊慌地擦乾眼泪看过来时,他又已经走远,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玉漱一开始並没注意到这个偶尔出现的年轻太监。但次数多了,她隱隱感觉到有些不一样。
手上的药膏,偶尔能分到多一点的食物,那个在她最无助时帮她解围的身影……她不確定是不是同一个人,但心里存了一份疑惑和微弱的感激。
一次,玉漱被派去给一处偏僻宫室送洗好的衣物。回来时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冷雨,她迷路了,又冷又怕,缩在一个廊檐下发抖。
易小川刚好办完差事回来,远远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心里一紧,快步走过去。
“怎么在这儿?”
他开口,也儘量温柔。
玉漱嚇了一跳,抬头看见是他,认出是那个帮过她的管事太监,心里稍安,但又立刻低下头,小声道:
“迷……迷路了……”
雨打湿了她的头髮和单薄的衣衫,冷得她嘴唇发紫,身子微微发抖,看起来可怜极了。
易小川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
他看了看四周,迅速脱下自己那件还算厚实的外衫,不由分说地披在她身上。
“穿上,跟我走。”
他的语气带著命令,玉漱从没没感受过的霸道。
玉漱愣住了,感受著带著陌生男子体温的衣衫,脸颊莫名一热,心跳得快了些。
“这……不合规矩……”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冻死在这里?”
易小川打断她,声音压得很低,“不想惹麻烦就快点。”
他率先走在前面,步伐不快,確保她能跟上。七拐八绕,很快就把她带回了织造处附近。
“前面就到了,你自己进去。”
易小川停下脚步,接过她递还的、已经半湿的外衫,低声快速说,
“以后机灵点,认认路。”
玉漱看著他被雨打湿的侧脸,心里百感交集,鼓起勇气问:
“你……你为什么帮我?”
易小川身体僵了一下,没有看她,只是望著远处的雨幕,沉默了片刻,才含糊地说:
“宫里活著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快步消失在雨夜里。
玉漱站在原地,看著他消失的方向,心里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这个沉默寡言、似乎总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太监,成了她在这冰冷深宫里,唯一一点模糊的依靠。
而易小川,走在回去的路上,冷雨打在他脸上,心里却一片滚烫。他知道自己不该这样,这很危险。
但那种暗中守护一个人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好像又变回了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只知道往上爬的怪物。
他摸了摸胸口那虎形烙印,眼神复杂。
“玉漱……”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