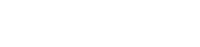刘公公收了东西,那张老脸鬆快了些,看易小川的眼神也少了点挑剔,多了点打量。
“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见儿。以后机灵点,亏待不了你。”
易小川腰弯得更低了,脸上堆著笑:
“谢公公提点,小川一定好好干。”
打这儿起,易小川算是在刘公公手底下掛了號。
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刘公公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让干什么脏活就干什么脏活。
永巷里有个老太监,人有点迂,不懂巴结,就因为一次送东西慢了点,惹刘公公不痛快。
刘公公没明说,只哼了一声:“这老货,腿脚是不利索了。”
易小川听懂了。
趁那老太监晚上起夜,偷偷在他常走的一段湿滑石阶上泼了层薄薄的油。
第二天,老太监摔断了腿,悽惨地叫了半天,最后被拖走了,不知死活。
易小川站在人群后面,面无表情地看著,心里木木的,只有一丝“办成了事”的麻木感。
晚上他躲在被窝里乾呕了几声,然后用力掐了自己大腿一把,把那点残存的噁心压了下去。
刘公公对此很满意,觉得这新来的蛋子果然“开窍”,用著顺手,渐渐把一些剋扣份例、打压不听话的小太监的活儿也交给他。
易小川干这些事越来越顺手。他发现自己以前在现代社会那点所谓的“善念”和“底线”,在这地方屁用没有,只会让自己更惨。
要想活,要想爬,就得比他们更狠、更毒。
他鞍前马后地伺候刘公公,捶腿捏肩,说奉承话,同时眼睛也没閒著,仔细观察刘公公是怎么管人、怎么捞油水、怎么跟上面打交道的。
他识字,所以会偷偷看宫里废弃的文书,琢磨那些弯弯绕绕。
他对下欺压,对上諂媚。整治不听话的小太监时,他下手黑,但偶尔,又会偷偷给那些被罚饿饭的人塞半块饼子,低声说句:
“兄弟,没办法,上头盯著呢,忍著点。”
这点小恩小惠,居然也让他拉拢了两个饿昏了头的小子,算是有了最初的眼线。
他知道刘公公这人贪財又胆小心眼小,成不了大气候,永巷这地方也没什么大油水。
他得找机会跳出去。
机会来了。
宫里要大宴,需要抽调人手去帮忙。
这是个露脸的活儿,虽然累,但有机会被更上层的管事看见。刘公公自然把自己几个心腹名字报了上去,没易小川的份。
易小川提前从他那两个眼线那儿得了信。他心一横,把自己进宫时藏的最后一点碎银偷偷塞给了来挑人的那位膳房管事太监身边的小徒,传了句话:
“永巷小川子,手脚麻利,嘴严,懂规矩,求公公给个机会。”
同时,他又故意在刘公公面前犯了个小错,惹得刘公公正当著一眾手下的面发火,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罚他去洗所有马桶,明確表示宴席的事没他的份。
这苦肉计做得十足。
宴席筹备那天,刘公公带著人趾高气扬地去了。
易小川埋头刷马桶。
等到宴席正日子,人手最紧缺的时候,那个膳房管事太监“偶然”路过永巷,皱著眉头看著刷马桶的易小川,像是突然想起来:
“你?就是小川子?这儿有个缺,赶紧跟我走,手脚利索点!”
刘公公在后厨忙得脚不沾烟,突然看到易小川低眉顺眼地出现,一惊,刚要发作,那膳房管事就嚷嚷:
“老刘,借你个人手用用,这小子看著还行。”
刘公公有火发不出,只能狠狠瞪了易小川一眼。
易小川在宴席后台拼了命地表现,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那位膳房管事伺候得舒舒服服。
宴席结束后,管事对他点了头:
“嗯,不错。回头我跟內务府说说,调你来膳房帮忙。”
易小川千恩万谢。
回去后,刘公公果然暴怒,觉得他背主求荣,要收拾他。
易小川直接跪下了,不是求饶,压低声音说:
“公公息怒。小川去了膳房,也是您的人。那儿油水厚,路子多,小川得了好处,能不孝敬您吗?总比一辈子困在这永巷强吧?小川若好了,您脸上也有光不是?”
刘公公被他说得一愣,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个道理,火气消了点,但还是骂骂咧咧了几句,警告他別忘了根本。
易小川顺利调到了膳房,虽然还是底层,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他更加如鱼得水,揣摩人心、溜须拍马、栽赃陷害的手段越发纯熟。
他很快巴结上了膳房更大的头头,悄悄把从刘公公那儿知道的一些贪墨小把柄递了上去。
没多久,刘公公就因为“办事不力,苛待下属”被擼了永巷的差事,打发去了更糟的地方。
易小川听到消息,只是淡淡“哦”了一声,继续忙手里的活。
旧主没了,他爬得更安心了。
他一步步往上钻营,从膳房又想办法调到了负责宫室清扫整理的部门,这里更容易接触到各宫娘娘、得势宦官的信息。
他变得越发阴沉老练,心里的算盘噼啪作响。他靠著告密、背刺、逢迎,慢慢混成了一个小管事,手底下也管著十几號人。
但这远远不够。
秦王贏乐修仙,对宫廷控制极严,尤其忌讳底下人接触修炼之事。
宫里的侍卫都是严格筛选的,宦官宫女更是严禁修炼,一旦发现,立刻处死。
只有那些最顶层、最得贏乐信任的老怪物,或许才被赏赐一点延年益寿的丹药皮毛。
易小川能感觉到,自己身体虽然因为吃喝稍好没那么虚弱了,但本质上还是那个被去势的残缺之人,带著一股阴柔气,力量微弱。
这让他感到绝望,物理上的差距,似乎不是靠阴谋诡计能弥补的。
但是,作为天选配角,掛还是要给他的
——
一天夜里,易小川奉命带人检查几处閒置偏殿的防火。
在一处极为偏僻、几乎半荒废的旧殿阁楼顶上,他踩鬆了一块瓦片,差点摔下去。手忙脚乱抓住房梁时,却摸到一个硬物。
那东西卡在梁木的缝隙里,满是灰尘。他抠出来,借著月光一看,是一个造型古拙的虎型玉佩,材质不明,触手冰凉,那虎形雕刻得异常凶猛,仿佛要扑噬人。
他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擦乾净灰尘,把它揣进了怀里。回去后,越看越觉得这玉佩不寻常,那虎似乎有生命一般。他试著把它戴在脖子上。
刚贴上皮肤,那玉佩猛地变得滚烫!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呃啊!”
易小川猝不及防,痛得低吼一声,想扯下来,那玉佩却像长在了他胸口一样!
剧烈的灼痛持续了將近十息,才猛地消退。他大汗淋漓地瘫倒在地,扯开衣襟一看,胸口心臟位置,赫然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暗红色的虎形烙印,像是天生就长在那里。
而那块玉佩,消失不见了。
他惊疑不定,但接下来的几天,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產生奇异的变化。
首先,力气变大了。以前扛一袋米都喘,现在单手就能提起来。身体似乎结实了很多,肌肉线条隱约重现,那种太监常见的虚浮阴柔感在快速消退,皮肤下的气血似乎都旺盛起来,连带著声音都浑厚了些许,不再那么尖细。感官也变得敏锐,能听到更远的声音,看得更清楚。
最神奇的是,他感觉下腹丹田位置,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从未有过的暖流在流动,虽然细微,却真实存在。
这变化让他又惊又喜!但他立刻把这惊喜死死按捺下去。他深知这变化在秦宫里有多危险。嬴政多疑,严禁內侍修炼,这虎形玉佩带来的改变,万一被人察觉,就是杀身之祸。
他更加小心地隱藏自己。白天,他依旧是那个低眉顺眼、行事谨慎的管事太监,甚至故意偶尔显得柔弱一点。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时,他才敢悄悄感受体內那丝微弱的气流,尝试著引导它——虽然他完全不懂修炼法门,只能凭感觉乱试。
那虎形烙印再无异状,但潜移默化地改变著他的体质。他看著铜镜里的自己,脸色红润了些,眼神深处那点因为残缺而带来的自卑和阴鬱似乎被一股隱而不发的凶悍之气逐渐取代。
他抚摸著胸口那滚烫的烙印,
“赵高……”他低声自语,这个名字如今已成了他野心的代號。
“这条路,我走定了。”
“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见儿。以后机灵点,亏待不了你。”
易小川腰弯得更低了,脸上堆著笑:
“谢公公提点,小川一定好好干。”
打这儿起,易小川算是在刘公公手底下掛了號。
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刘公公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让干什么脏活就干什么脏活。
永巷里有个老太监,人有点迂,不懂巴结,就因为一次送东西慢了点,惹刘公公不痛快。
刘公公没明说,只哼了一声:“这老货,腿脚是不利索了。”
易小川听懂了。
趁那老太监晚上起夜,偷偷在他常走的一段湿滑石阶上泼了层薄薄的油。
第二天,老太监摔断了腿,悽惨地叫了半天,最后被拖走了,不知死活。
易小川站在人群后面,面无表情地看著,心里木木的,只有一丝“办成了事”的麻木感。
晚上他躲在被窝里乾呕了几声,然后用力掐了自己大腿一把,把那点残存的噁心压了下去。
刘公公对此很满意,觉得这新来的蛋子果然“开窍”,用著顺手,渐渐把一些剋扣份例、打压不听话的小太监的活儿也交给他。
易小川干这些事越来越顺手。他发现自己以前在现代社会那点所谓的“善念”和“底线”,在这地方屁用没有,只会让自己更惨。
要想活,要想爬,就得比他们更狠、更毒。
他鞍前马后地伺候刘公公,捶腿捏肩,说奉承话,同时眼睛也没閒著,仔细观察刘公公是怎么管人、怎么捞油水、怎么跟上面打交道的。
他识字,所以会偷偷看宫里废弃的文书,琢磨那些弯弯绕绕。
他对下欺压,对上諂媚。整治不听话的小太监时,他下手黑,但偶尔,又会偷偷给那些被罚饿饭的人塞半块饼子,低声说句:
“兄弟,没办法,上头盯著呢,忍著点。”
这点小恩小惠,居然也让他拉拢了两个饿昏了头的小子,算是有了最初的眼线。
他知道刘公公这人贪財又胆小心眼小,成不了大气候,永巷这地方也没什么大油水。
他得找机会跳出去。
机会来了。
宫里要大宴,需要抽调人手去帮忙。
这是个露脸的活儿,虽然累,但有机会被更上层的管事看见。刘公公自然把自己几个心腹名字报了上去,没易小川的份。
易小川提前从他那两个眼线那儿得了信。他心一横,把自己进宫时藏的最后一点碎银偷偷塞给了来挑人的那位膳房管事太监身边的小徒,传了句话:
“永巷小川子,手脚麻利,嘴严,懂规矩,求公公给个机会。”
同时,他又故意在刘公公面前犯了个小错,惹得刘公公正当著一眾手下的面发火,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罚他去洗所有马桶,明確表示宴席的事没他的份。
这苦肉计做得十足。
宴席筹备那天,刘公公带著人趾高气扬地去了。
易小川埋头刷马桶。
等到宴席正日子,人手最紧缺的时候,那个膳房管事太监“偶然”路过永巷,皱著眉头看著刷马桶的易小川,像是突然想起来:
“你?就是小川子?这儿有个缺,赶紧跟我走,手脚利索点!”
刘公公在后厨忙得脚不沾烟,突然看到易小川低眉顺眼地出现,一惊,刚要发作,那膳房管事就嚷嚷:
“老刘,借你个人手用用,这小子看著还行。”
刘公公有火发不出,只能狠狠瞪了易小川一眼。
易小川在宴席后台拼了命地表现,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那位膳房管事伺候得舒舒服服。
宴席结束后,管事对他点了头:
“嗯,不错。回头我跟內务府说说,调你来膳房帮忙。”
易小川千恩万谢。
回去后,刘公公果然暴怒,觉得他背主求荣,要收拾他。
易小川直接跪下了,不是求饶,压低声音说:
“公公息怒。小川去了膳房,也是您的人。那儿油水厚,路子多,小川得了好处,能不孝敬您吗?总比一辈子困在这永巷强吧?小川若好了,您脸上也有光不是?”
刘公公被他说得一愣,仔细一想,好像是这个道理,火气消了点,但还是骂骂咧咧了几句,警告他別忘了根本。
易小川顺利调到了膳房,虽然还是底层,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他更加如鱼得水,揣摩人心、溜须拍马、栽赃陷害的手段越发纯熟。
他很快巴结上了膳房更大的头头,悄悄把从刘公公那儿知道的一些贪墨小把柄递了上去。
没多久,刘公公就因为“办事不力,苛待下属”被擼了永巷的差事,打发去了更糟的地方。
易小川听到消息,只是淡淡“哦”了一声,继续忙手里的活。
旧主没了,他爬得更安心了。
他一步步往上钻营,从膳房又想办法调到了负责宫室清扫整理的部门,这里更容易接触到各宫娘娘、得势宦官的信息。
他变得越发阴沉老练,心里的算盘噼啪作响。他靠著告密、背刺、逢迎,慢慢混成了一个小管事,手底下也管著十几號人。
但这远远不够。
秦王贏乐修仙,对宫廷控制极严,尤其忌讳底下人接触修炼之事。
宫里的侍卫都是严格筛选的,宦官宫女更是严禁修炼,一旦发现,立刻处死。
只有那些最顶层、最得贏乐信任的老怪物,或许才被赏赐一点延年益寿的丹药皮毛。
易小川能感觉到,自己身体虽然因为吃喝稍好没那么虚弱了,但本质上还是那个被去势的残缺之人,带著一股阴柔气,力量微弱。
这让他感到绝望,物理上的差距,似乎不是靠阴谋诡计能弥补的。
但是,作为天选配角,掛还是要给他的
——
一天夜里,易小川奉命带人检查几处閒置偏殿的防火。
在一处极为偏僻、几乎半荒废的旧殿阁楼顶上,他踩鬆了一块瓦片,差点摔下去。手忙脚乱抓住房梁时,却摸到一个硬物。
那东西卡在梁木的缝隙里,满是灰尘。他抠出来,借著月光一看,是一个造型古拙的虎型玉佩,材质不明,触手冰凉,那虎形雕刻得异常凶猛,仿佛要扑噬人。
他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擦乾净灰尘,把它揣进了怀里。回去后,越看越觉得这玉佩不寻常,那虎似乎有生命一般。他试著把它戴在脖子上。
刚贴上皮肤,那玉佩猛地变得滚烫!像一块烧红的烙铁!
“呃啊!”
易小川猝不及防,痛得低吼一声,想扯下来,那玉佩却像长在了他胸口一样!
剧烈的灼痛持续了將近十息,才猛地消退。他大汗淋漓地瘫倒在地,扯开衣襟一看,胸口心臟位置,赫然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暗红色的虎形烙印,像是天生就长在那里。
而那块玉佩,消失不见了。
他惊疑不定,但接下来的几天,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產生奇异的变化。
首先,力气变大了。以前扛一袋米都喘,现在单手就能提起来。身体似乎结实了很多,肌肉线条隱约重现,那种太监常见的虚浮阴柔感在快速消退,皮肤下的气血似乎都旺盛起来,连带著声音都浑厚了些许,不再那么尖细。感官也变得敏锐,能听到更远的声音,看得更清楚。
最神奇的是,他感觉下腹丹田位置,似乎有了一丝微弱的、从未有过的暖流在流动,虽然细微,却真实存在。
这变化让他又惊又喜!但他立刻把这惊喜死死按捺下去。他深知这变化在秦宫里有多危险。嬴政多疑,严禁內侍修炼,这虎形玉佩带来的改变,万一被人察觉,就是杀身之祸。
他更加小心地隱藏自己。白天,他依旧是那个低眉顺眼、行事谨慎的管事太监,甚至故意偶尔显得柔弱一点。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时,他才敢悄悄感受体內那丝微弱的气流,尝试著引导它——虽然他完全不懂修炼法门,只能凭感觉乱试。
那虎形烙印再无异状,但潜移默化地改变著他的体质。他看著铜镜里的自己,脸色红润了些,眼神深处那点因为残缺而带来的自卑和阴鬱似乎被一股隱而不发的凶悍之气逐渐取代。
他抚摸著胸口那滚烫的烙印,
“赵高……”他低声自语,这个名字如今已成了他野心的代號。
“这条路,我走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