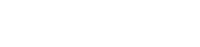几个如狼似虎的宫廷侍卫扑上来,扭住易小川的胳膊就往外拖。
“等等!秦王!嬴政!你说清楚!你怎么认识高要的!你是不是现代人!喂!!”
易小川疯狂挣扎,嘶吼著,语无伦次。但没人理会他。齐典大夫嚇得面无人色,自身难保。
卫庄生死不知。他被粗暴地拖离了大殿,身后的王座上,贏乐的表情冷漠而模糊。
他没有被拖去牢房,而是被扔进了一间昏暗的偏房,散发著霉味和淡淡血腥气。
门从外面锁上了。无论他怎么拍打吼叫,都无人应答。
第一天,没人理他。又渴又饿,恐惧像毒蛇啃噬著他的內心。
第二天,来了个面无表情的老宦官,丟给他两个硬得像石头的窝窝头和一碗清水。
易小川抓住机会急问:
“这到底怎么回事?秦王他……”
老宦官看都没看他一眼,转身走了。
第三天,还是那个老宦官,带来的食物变了:一小碗几乎没放盐的煮黄豆,还有两个白水煮蛋,但只给了蛋黄,蛋白不知去了哪里。
易小川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蛋黄噎得他直伸脖子,但他没多想。
第四天,第五天……接连几天,食物都是如此:少量的水,硬窝头或者煮豆子,以及每天两个干噎的蛋黄。
他开始感到不对劲,身体莫名地燥热,小便变得困难,有种火辣辣的刺痛感。他问送饭的人,得到的只有沉默。
他终於反应过来,这是在“准备”了。他在一些杂书上看过,古代太监净身前,要有一段时间的特殊饮食,清空肠胃,蛋黄据说是为了……
他不敢再想下去,恐惧瞬间淹没了他。
“不!不行!放开我!我不是太监!我是易小川!我是从21世纪来的!你们不能这样!!”
他发疯似的撞门,嘶吼,直到嗓子哑了,力气耗尽,滑坐在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也许七八天,也许十来天。门终於再次打开。进来的不是那个老宦官,而是几个身材粗壮的杂役太监。
易小川被他们死死按住,挣扎完全是徒劳。
他被扒掉了衣服,用破布堵住了嘴,像牲口一样被抬了出去,穿过阴森漫长的宫道,进入一间更加昏暗、药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屋子里。
屋中间有一张带著皮扣的“床”。
他看到旁边放著各种说不清形状的、闪著寒光的金属工具。
一个戴著布巾、眼神麻木的老者正在用火烤著一把小小的、弯月状的利刃。
易小川的瞳孔缩成了针尖,恐惧和绝望让他发出了“呜呜”的哀鸣,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他拼命摇头,但身体被死死按在那张“床”上,皮扣扣紧了他的手腕脚踝。
那老者走了过来,看了他一眼。
然后,下身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传来!
易小川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
……
再次醒来时,他躺在一条大通铺上,周围是几个和他一样年轻的脸孔。
下身火烧火燎地疼,动一下都钻心。空气里瀰漫著草药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颓败气息。
一个老宦官——不是行刑的那个——走过来,粗暴地给他换药。
动作机械,没有丝毫温柔可言。易小川疼得浑身抽搐,咬破了嘴唇。
“嗯……哼……”
老宦官发出意味不明的哼声,算是交代了几句这里的规矩:这里是蚕室,他们这些新“净身”的,都得在这里养伤。伤好了,才能分配去处。少说话,多躺著,憋著尿,能活下来就算造化。
易小川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低矮、骯脏的屋顶。
身体的剧痛比不上心里的万分之一。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不再是男人了……
他成了一个阉人,一个太监。
屈辱和痛苦几乎將他撕裂。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秦王嬴政,他到底是谁?
他怎么会知道高要?他明明知道高要,知道现代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这样对自己?如果真是老乡,不该互相帮助吗?难道他不是老乡?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
“高要……高要……”
他在心里吶喊,“贏乐怎么会认识你?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像毒虫一样日夜不停地啃噬著他的理智。
成为太监的事实已经足够摧毁一个人,而这个巨大的、无解的谜团,更是让他的痛苦加倍,陷入一种疯狂边缘的迷茫。
伤口的疼痛反覆提醒他遭遇的酷刑。
蚕室里的日子暗无天日,每天就是换药、喝点稀粥、躺著。周围的人要么麻木,要么在睡梦中哭泣呻吟。管事的太监动不动就打骂,態度极其恶劣。
易小川艰难地適应著,学著像其他人一样蜷缩起来,降低存在感。
但內心的火焰没有完全熄灭。屈辱、痛苦、仇恨,还有那个巨大的疑问——“贏乐和高要”——支撑著他,让他吊著最后一口气。
他要活下去。他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否则,他死也不甘心。
……
……
易小川在蚕室挨过了最难受的那段日子。
伤口结痂,能下地走动了,虽然姿势还有点彆扭,胯下总是隱隱作痛,提醒他那场永世不忘的噩梦。
他被分到了永巷,就是宫里专门管杂役洒扫的地方,归一个姓刘的老宦官管。
这地方,是宫里的最底层,比冷宫还不如。来的都是没门路、没银子打点的倒霉蛋。
天不亮就得起来,扛著比人还高的大扫帚,清扫漫长的宫道。
落叶好像永远扫不完,刚扫乾净一阵风又吹来一堆。要么就是去刷洗那些不知道多少年没彻底清理过的恭桶,恶臭能熏得人把隔夜饭吐出来。
冬天,手浸在冰水里,冻得裂开血口子。夏天,闷在低矮的杂物房里整理堆积如山的旧物,汗流浹背,蚊虫叮咬。
饭食永远是餿的、冷的,勉强能入口。就那么一点量,还经常被管事的、或者先来的老油子剋扣。
易小川试过爭辩,换来的是一顿拳打脚踢,或者更脏更累的活儿。
“看什么看?新来的蛋子,懂不懂规矩!”
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太监经常找他麻烦,叫他“蛋子”,是笑话他新净身。
易小川咬著牙,低下头。
他打不过,也没地方说理。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憋著一股邪火,变著法地往下欺负,寻找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
晚上睡大通铺,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汗臭、脚臭、还有伤口化脓的臭味混在一起。呼嚕声、磨牙声、梦话哭声,几乎没有一夜安寧。
易小川缩在角落里,常常睁眼到天亮。身体的疲惫和心里的屈辱交织在一起。
他脑子里反覆就转著那几个问题:贏乐为什么知道高要?他是不是老乡?如果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他想起看过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里面的赵高,后来成了权倾朝野的赵高。
对,赵高!秦朝最大的太监头子!
一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如果能找到赵高,抱上他的大腿……是不是就能活下去?甚至……有机会报復嬴政?至少,能弄明白那个问题!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听。趁著给一个看起来稍微面善的老宦官捶腿的机会,他低声下气地问:
“公公,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宫里有没有一位叫赵高的公公?”
老宦官眯著眼享受,哼了一声:
“赵高?哪个犄角旮旯的?没听说过。”
易小川不死心,以为对方没听清,又补充:“就是……可能权力很大的那种,在中车府什么的……”
老宦官不耐烦地推开他:
“中车府?那是陛下近侍待的地方,轮得到咱们打听?滚一边去,没用的东西。”
易小川又试了几次,问不同的人,甚至偷偷塞了半个藏了好几天、已经干硬的窝窝头给一个负责传递物品的小火者。
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没听过赵高这人。
一开始是失望,后来变成了困惑,最后是恐惧。
怎么会没有赵高?《大秦帝国》里明明有!
难道歷史不一样?还是我记错了?或者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我知道的那个秦朝?
嬴政的异常,仙丹,修士……没有赵高……
这个发现比单纯的受苦更让他害怕。他最后的指望,那个看似荒谬但能支撑他忍下去的剧本,碎了。他连抱大腿的对象都没有。
那天下午,他又被那个横肉太监找茬,说他扫地扬起了灰,衝撞了不知道哪路贵人路过留下的“气”,被罚跪在永巷口两个时辰。
膝盖硌在冰冷的石板上,路过的宫女太监投来或怜悯或讥讽的目光。
羞辱和绝望达到了顶点。
晚上,他躺在臭气熏天的通铺上,听著周围的鼾声,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体很累,但脑子异常清醒。
没有赵高。
没有大腿可抱。
贏乐知道高要,然后突然把他变成太监。
这个世界疯了,或者说,他掉进了一个完全错误、更加残酷的版本里。
那就……
一个念头从他心底的最深处,慢慢地钻了出来。
既然没有赵高……
那老子就来当这个赵高!
原歷史能有赵高,我易小川为什么不能成为赵高?
嬴政,你等著。
你留我一条命,是你最大的错误。
你不知道我们这种人,从现代来的,最知道什么叫生存,什么叫忍,什么叫……往上爬!
他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几乎掐出血来。
身体因为激动和仇恨微微发抖。
从第二天起,易小川变了。
扫地把边边角角都扫得乾乾净净,一声不吭。刷恭桶刷得比別人都亮。分配活计,抢著干最累的。对管事的刘公公,极尽諂媚,有机会就上去点头哈腰,说几句討巧的话,虽然说得彆扭,但他强迫自己说。
他把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省下一半,偷偷塞给刘公公。
刘公公眯著眼打量他:
“小子,开窍了?”
易小川挤出一个卑微的笑:“全靠公公栽培,赏口饭吃。”
他不再打听赵高,开始拼命打听宫里的规矩,各个宫殿的主子,得势的宦官都是谁,有什么喜好。他观察那些混得稍微好点的太监是怎么说话办事的。
他学得很快。因为恨和求生欲,是最好的老师。
“等等!秦王!嬴政!你说清楚!你怎么认识高要的!你是不是现代人!喂!!”
易小川疯狂挣扎,嘶吼著,语无伦次。但没人理会他。齐典大夫嚇得面无人色,自身难保。
卫庄生死不知。他被粗暴地拖离了大殿,身后的王座上,贏乐的表情冷漠而模糊。
他没有被拖去牢房,而是被扔进了一间昏暗的偏房,散发著霉味和淡淡血腥气。
门从外面锁上了。无论他怎么拍打吼叫,都无人应答。
第一天,没人理他。又渴又饿,恐惧像毒蛇啃噬著他的內心。
第二天,来了个面无表情的老宦官,丟给他两个硬得像石头的窝窝头和一碗清水。
易小川抓住机会急问:
“这到底怎么回事?秦王他……”
老宦官看都没看他一眼,转身走了。
第三天,还是那个老宦官,带来的食物变了:一小碗几乎没放盐的煮黄豆,还有两个白水煮蛋,但只给了蛋黄,蛋白不知去了哪里。
易小川饿极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蛋黄噎得他直伸脖子,但他没多想。
第四天,第五天……接连几天,食物都是如此:少量的水,硬窝头或者煮豆子,以及每天两个干噎的蛋黄。
他开始感到不对劲,身体莫名地燥热,小便变得困难,有种火辣辣的刺痛感。他问送饭的人,得到的只有沉默。
他终於反应过来,这是在“准备”了。他在一些杂书上看过,古代太监净身前,要有一段时间的特殊饮食,清空肠胃,蛋黄据说是为了……
他不敢再想下去,恐惧瞬间淹没了他。
“不!不行!放开我!我不是太监!我是易小川!我是从21世纪来的!你们不能这样!!”
他发疯似的撞门,嘶吼,直到嗓子哑了,力气耗尽,滑坐在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也许七八天,也许十来天。门终於再次打开。进来的不是那个老宦官,而是几个身材粗壮的杂役太监。
易小川被他们死死按住,挣扎完全是徒劳。
他被扒掉了衣服,用破布堵住了嘴,像牲口一样被抬了出去,穿过阴森漫长的宫道,进入一间更加昏暗、药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屋子里。
屋中间有一张带著皮扣的“床”。
他看到旁边放著各种说不清形状的、闪著寒光的金属工具。
一个戴著布巾、眼神麻木的老者正在用火烤著一把小小的、弯月状的利刃。
易小川的瞳孔缩成了针尖,恐惧和绝望让他发出了“呜呜”的哀鸣,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
他拼命摇头,但身体被死死按在那张“床”上,皮扣扣紧了他的手腕脚踝。
那老者走了过来,看了他一眼。
然后,下身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传来!
易小川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
……
再次醒来时,他躺在一条大通铺上,周围是几个和他一样年轻的脸孔。
下身火烧火燎地疼,动一下都钻心。空气里瀰漫著草药味和一种难以形容的颓败气息。
一个老宦官——不是行刑的那个——走过来,粗暴地给他换药。
动作机械,没有丝毫温柔可言。易小川疼得浑身抽搐,咬破了嘴唇。
“嗯……哼……”
老宦官发出意味不明的哼声,算是交代了几句这里的规矩:这里是蚕室,他们这些新“净身”的,都得在这里养伤。伤好了,才能分配去处。少说话,多躺著,憋著尿,能活下来就算造化。
易小川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低矮、骯脏的屋顶。
身体的剧痛比不上心里的万分之一。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不再是男人了……
他成了一个阉人,一个太监。
屈辱和痛苦几乎將他撕裂。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秦王嬴政,他到底是谁?
他怎么会知道高要?他明明知道高要,知道现代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这样对自己?如果真是老乡,不该互相帮助吗?难道他不是老乡?那这一切又怎么解释?
“高要……高要……”
他在心里吶喊,“贏乐怎么会认识你?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问题,像毒虫一样日夜不停地啃噬著他的理智。
成为太监的事实已经足够摧毁一个人,而这个巨大的、无解的谜团,更是让他的痛苦加倍,陷入一种疯狂边缘的迷茫。
伤口的疼痛反覆提醒他遭遇的酷刑。
蚕室里的日子暗无天日,每天就是换药、喝点稀粥、躺著。周围的人要么麻木,要么在睡梦中哭泣呻吟。管事的太监动不动就打骂,態度极其恶劣。
易小川艰难地適应著,学著像其他人一样蜷缩起来,降低存在感。
但內心的火焰没有完全熄灭。屈辱、痛苦、仇恨,还有那个巨大的疑问——“贏乐和高要”——支撑著他,让他吊著最后一口气。
他要活下去。他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否则,他死也不甘心。
……
……
易小川在蚕室挨过了最难受的那段日子。
伤口结痂,能下地走动了,虽然姿势还有点彆扭,胯下总是隱隱作痛,提醒他那场永世不忘的噩梦。
他被分到了永巷,就是宫里专门管杂役洒扫的地方,归一个姓刘的老宦官管。
这地方,是宫里的最底层,比冷宫还不如。来的都是没门路、没银子打点的倒霉蛋。
天不亮就得起来,扛著比人还高的大扫帚,清扫漫长的宫道。
落叶好像永远扫不完,刚扫乾净一阵风又吹来一堆。要么就是去刷洗那些不知道多少年没彻底清理过的恭桶,恶臭能熏得人把隔夜饭吐出来。
冬天,手浸在冰水里,冻得裂开血口子。夏天,闷在低矮的杂物房里整理堆积如山的旧物,汗流浹背,蚊虫叮咬。
饭食永远是餿的、冷的,勉强能入口。就那么一点量,还经常被管事的、或者先来的老油子剋扣。
易小川试过爭辩,换来的是一顿拳打脚踢,或者更脏更累的活儿。
“看什么看?新来的蛋子,懂不懂规矩!”
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太监经常找他麻烦,叫他“蛋子”,是笑话他新净身。
易小川咬著牙,低下头。
他打不过,也没地方说理。这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憋著一股邪火,变著法地往下欺负,寻找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
晚上睡大通铺,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汗臭、脚臭、还有伤口化脓的臭味混在一起。呼嚕声、磨牙声、梦话哭声,几乎没有一夜安寧。
易小川缩在角落里,常常睁眼到天亮。身体的疲惫和心里的屈辱交织在一起。
他脑子里反覆就转著那几个问题:贏乐为什么知道高要?他是不是老乡?如果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他想起看过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里面的赵高,后来成了权倾朝野的赵高。
对,赵高!秦朝最大的太监头子!
一个念头像野草一样在他心里疯长:如果能找到赵高,抱上他的大腿……是不是就能活下去?甚至……有机会报復嬴政?至少,能弄明白那个问题!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打听。趁著给一个看起来稍微面善的老宦官捶腿的机会,他低声下气地问:
“公公,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宫里有没有一位叫赵高的公公?”
老宦官眯著眼享受,哼了一声:
“赵高?哪个犄角旮旯的?没听说过。”
易小川不死心,以为对方没听清,又补充:“就是……可能权力很大的那种,在中车府什么的……”
老宦官不耐烦地推开他:
“中车府?那是陛下近侍待的地方,轮得到咱们打听?滚一边去,没用的东西。”
易小川又试了几次,问不同的人,甚至偷偷塞了半个藏了好几天、已经干硬的窝窝头给一个负责传递物品的小火者。
得到的回答都一样:没听过赵高这人。
一开始是失望,后来变成了困惑,最后是恐惧。
怎么会没有赵高?《大秦帝国》里明明有!
难道歷史不一样?还是我记错了?或者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我知道的那个秦朝?
嬴政的异常,仙丹,修士……没有赵高……
这个发现比单纯的受苦更让他害怕。他最后的指望,那个看似荒谬但能支撑他忍下去的剧本,碎了。他连抱大腿的对象都没有。
那天下午,他又被那个横肉太监找茬,说他扫地扬起了灰,衝撞了不知道哪路贵人路过留下的“气”,被罚跪在永巷口两个时辰。
膝盖硌在冰冷的石板上,路过的宫女太监投来或怜悯或讥讽的目光。
羞辱和绝望达到了顶点。
晚上,他躺在臭气熏天的通铺上,听著周围的鼾声,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体很累,但脑子异常清醒。
没有赵高。
没有大腿可抱。
贏乐知道高要,然后突然把他变成太监。
这个世界疯了,或者说,他掉进了一个完全错误、更加残酷的版本里。
那就……
一个念头从他心底的最深处,慢慢地钻了出来。
既然没有赵高……
那老子就来当这个赵高!
原歷史能有赵高,我易小川为什么不能成为赵高?
嬴政,你等著。
你留我一条命,是你最大的错误。
你不知道我们这种人,从现代来的,最知道什么叫生存,什么叫忍,什么叫……往上爬!
他猛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掌心,几乎掐出血来。
身体因为激动和仇恨微微发抖。
从第二天起,易小川变了。
扫地把边边角角都扫得乾乾净净,一声不吭。刷恭桶刷得比別人都亮。分配活计,抢著干最累的。对管事的刘公公,极尽諂媚,有机会就上去点头哈腰,说几句討巧的话,虽然说得彆扭,但他强迫自己说。
他把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省下一半,偷偷塞给刘公公。
刘公公眯著眼打量他:
“小子,开窍了?”
易小川挤出一个卑微的笑:“全靠公公栽培,赏口饭吃。”
他不再打听赵高,开始拼命打听宫里的规矩,各个宫殿的主子,得势的宦官都是谁,有什么喜好。他观察那些混得稍微好点的太监是怎么说话办事的。
他学得很快。因为恨和求生欲,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