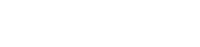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45章 这是拒马步
浆洗晾晒,全归你管。”
毕竟还是少年人,前一刻还拧著脖子非要问个水落石出,后一刻就被姐姐几句话轻轻拨开,心思早飘到了別处。
一听姐姐鬆了口,薄近侯咧嘴傻笑,连连点头:“成!包在我身上!”
顾天白偏过头,静静望向姐姐。
这几日她言谈举止处处透著陌生——那副漫不经心的洒脱,那点若即若离的试探,全然不是从前那个沉静持重的姐姐。
他心头微沉,第一次尝到了隔膜的滋味。
仿佛感知到弟弟的目光,姐姐忽而侧首“望”来。
虽双目失明,可那空茫眸子里竟浮起一丝温软笑意,像雾里藏灯,淡却耐品。
她伸手接过弟弟手中酒碗,稳稳举过头顶。
昏月斜照,勾出她清瘦轮廓,喉间微动,清嗓一开,声如黄鸝穿林,悠扬又篤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教金樽空映月;流光不肯为人驻,有酒且歌且开顏!”
正啃著鸡骨架的薄近侯茫然抬头,望著那盲女举碗迎月的模样,虽不解词中深意,却只觉一股豪气扑面而来,直撞胸口。
眼看姐姐仰脖饮尽半盏残酒,顾天白甩开杂念,向后一靠,脊背贴上粗糲树干,朗声应和:
“有酒且歌且开顏,细嚼人间烟火味,笑看红尘万般色。”
晚饭散场时,薄近侯已让酒意熏得耳根泛红,却又一把拽住顾天白袖子,催他赶紧教那套“三式开山斧”。
这也难怪——他头回摸斧头,新奇劲儿还烧著呢。
谁年少时不做过仗剑走马的梦?
小时候只在说书摊前踮脚听、在旧画本里盯那些腾挪如燕、立马横刀的英姿,幻想有朝一日也能披风猎猎、快意纵横。
如今真人就在眼前,斧影就在手边,薄近侯如何按得住那颗怦怦直跳的心?
顾天白自幼练拳踩桩,见惯了江湖上那些踏雪无痕、摘叶伤人的成名人物,哪能真正懂薄近侯这火烧眉毛般的热切?
本想著依著“一日之计在於晨”的老理,让薄近侯明早迎著霜气、沾著露水再开练也不迟,可架不住他软磨硬泡、缠得人耳根发烫,只好拎起油灯,一脚踏进了院子。
院中没屋里的炭火暖意,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
这节气,连麻雀都缩在檐下不肯露头。
顾天白虽从小泡药浴、熬筋骨,一身內气流转几周天便能压住寒意,可心底仍厌烦这冻得人牙关打颤的夜风——不是扛不住,是懒得受这份罪。
他斜眼一扫,只见薄近侯只套了件单衣,袖口还卷到小臂,冻得指尖发白却挺得笔直。顾天白嘴角一抽,无声嗤笑。
月光沉厚,清亮如水。他抄手立在廊下,看薄近侯蹦跳著取下倚在门边的宣花巨斧,咧嘴傻乐,晃晃悠悠就站到了自己跟前。
“横斧於胸。”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101 看书网书库广,????????????.??????任你选 】
话音刚落,他转身便往屋里踱,冷是不怕,可暖烘烘的屋子总比这刺骨穿堂风强上十倍。
“然后呢?”薄近侯眼睛发亮,照著吩咐把斧子稳稳横在胸前。
“两腿分开,略宽於肩;膝盖微屈,大腿与地面平行;脚尖朝前,含胸收腹,脊背拔直。”
“这是拒马步。”薄近侯依著那二十四字口诀摆好架势,语气篤定。
顾天白已走到门口,手刚搭上门框,闻言一顿,扭过头来:“嗯,先扎马。”
薄近侯鼻尖一皱,满脸不以为然。
顾天白忍俊不禁:“练武不练功,老来一场空;练功不练腰,功夫难登高。
別嫌这马步闷,千百年来,想动拳脚,先蹲稳当——马步扎牢了,脚下才生根,对敌时才不被一撞就翻。否则別说三板斧,再玄的招式,下盘虚浮也是纸糊的架子。
你嘛,遇上个膀大腰圆的,三两下就得踉蹌跪地。”
薄近侯听不懂这些门道,咬紧牙关,硬是托著百斤巨斧蹲在那里。
顾天白閒得发慌,忽然记起前几日练过几趟、如今已有些生疏的七星连环步,便隨手捡了根枯枝,在冻土上匆匆划出北斗七宫,气沉丹田,足下生风,按著星位轨跡腾挪闪转。
约莫一炷香工夫,身上泛起热意,他收势停步,侧身一看——薄近侯早已摇摇欲坠,马步歪斜,身子前后晃荡,可那柄巨斧仍死死托在胸前,一寸未放,连喘息都压著嗓子,半分没歇。
这段时间看似短,对初学者却是最难熬的关口。
心急只会伤筋挫骨。
偏又寒风裹著湿气扑面而来,稍不留神,阴寒便顺著绷紧的筋络往里钻——轻则手脚僵麻,重则经脉滯涩,別说耍斧头,提桶水都打晃。
顾天白一步抢上前,伸手卸下巨斧,“哐当”甩在青砖地上。
薄近侯心头一紧,以为惹恼了师父,强撑著酸麻的胳膊腿想开口解释,却见顾天白反手攥住他手掌,十指交扣,旋身借力一送——“咳嘭”一声脆响,震得人耳膜嗡嗡。
还不等他回过神,顾天白手腕一收,拇指顺势沿他虎口向上疾点,合谷、列缺两穴应指而开;脚下毫不迟疑,连踏他双腿足三里、委中两处;
接著欺身贴近,右肩猛撞他怀中空门,左手翻飞如蝶,接连叩击中极、关元、石门、气海、神闕五处要穴;
最后一推一顶,借肩靠之势將他掀得离地后跃,左掌顺势滑入他臂弯,一绕一扣,四两拨千斤般轻巧一带——薄近侯整个人倏然挺直,钉在原地,纹丝不动。
说来冗长,实则电光石火。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薄近侯还懵著,像被风捲起的落叶,飘在半空没落地。
直到顾天白退开两步,他才猛然回魂,顿觉通体舒泰,毛孔张开如饮甘泉,五臟六腑熨帖得如同新蒸的软糕,方才火烧火燎的酸胀感,竟一丝不剩。
他忽然想起茶馆里说书先生拍案讲过的桥段,眼睛一亮,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替我冲开了任督二脉?”
顾天白愣住了。
这连门槛都没迈进去,別提什么调息引气的口诀了,怎么反倒冲开了任督二脉?
若真这么轻巧,满大街岂不全是踏雪无痕、摘叶飞花的宗师?
“你刚才扎马步太猛,筋骨绷得过紧,累了就该歇著再练——心急喝不了滚烫的豆腐脑,这道理都不懂?”
他抬手在薄近侯后颈一按一揉,“刚不过是替你鬆开几处滯涩的经络,免得明早浑身僵硬,连床都起不来。”
没等到自己盼著的答案,薄近侯顿时蔫了,嘴角垮下去,眉梢耷拉著,活像被秋霜扫过的嫩苗。
第445章 这是拒马步
浆洗晾晒,全归你管。”
毕竟还是少年人,前一刻还拧著脖子非要问个水落石出,后一刻就被姐姐几句话轻轻拨开,心思早飘到了別处。
一听姐姐鬆了口,薄近侯咧嘴傻笑,连连点头:“成!包在我身上!”
顾天白偏过头,静静望向姐姐。
这几日她言谈举止处处透著陌生——那副漫不经心的洒脱,那点若即若离的试探,全然不是从前那个沉静持重的姐姐。
他心头微沉,第一次尝到了隔膜的滋味。
仿佛感知到弟弟的目光,姐姐忽而侧首“望”来。
虽双目失明,可那空茫眸子里竟浮起一丝温软笑意,像雾里藏灯,淡却耐品。
她伸手接过弟弟手中酒碗,稳稳举过头顶。
昏月斜照,勾出她清瘦轮廓,喉间微动,清嗓一开,声如黄鸝穿林,悠扬又篤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教金樽空映月;流光不肯为人驻,有酒且歌且开顏!”
正啃著鸡骨架的薄近侯茫然抬头,望著那盲女举碗迎月的模样,虽不解词中深意,却只觉一股豪气扑面而来,直撞胸口。
眼看姐姐仰脖饮尽半盏残酒,顾天白甩开杂念,向后一靠,脊背贴上粗糲树干,朗声应和:
“有酒且歌且开顏,细嚼人间烟火味,笑看红尘万般色。”
晚饭散场时,薄近侯已让酒意熏得耳根泛红,却又一把拽住顾天白袖子,催他赶紧教那套“三式开山斧”。
这也难怪——他头回摸斧头,新奇劲儿还烧著呢。
谁年少时不做过仗剑走马的梦?
小时候只在说书摊前踮脚听、在旧画本里盯那些腾挪如燕、立马横刀的英姿,幻想有朝一日也能披风猎猎、快意纵横。
如今真人就在眼前,斧影就在手边,薄近侯如何按得住那颗怦怦直跳的心?
顾天白自幼练拳踩桩,见惯了江湖上那些踏雪无痕、摘叶伤人的成名人物,哪能真正懂薄近侯这火烧眉毛般的热切?
本想著依著“一日之计在於晨”的老理,让薄近侯明早迎著霜气、沾著露水再开练也不迟,可架不住他软磨硬泡、缠得人耳根发烫,只好拎起油灯,一脚踏进了院子。
院中没屋里的炭火暖意,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
这节气,连麻雀都缩在檐下不肯露头。
顾天白虽从小泡药浴、熬筋骨,一身內气流转几周天便能压住寒意,可心底仍厌烦这冻得人牙关打颤的夜风——不是扛不住,是懒得受这份罪。
他斜眼一扫,只见薄近侯只套了件单衣,袖口还卷到小臂,冻得指尖发白却挺得笔直。顾天白嘴角一抽,无声嗤笑。
月光沉厚,清亮如水。他抄手立在廊下,看薄近侯蹦跳著取下倚在门边的宣花巨斧,咧嘴傻乐,晃晃悠悠就站到了自己跟前。
“横斧於胸。”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101 看书网书库广,????????????.??????任你选 】
话音刚落,他转身便往屋里踱,冷是不怕,可暖烘烘的屋子总比这刺骨穿堂风强上十倍。
“然后呢?”薄近侯眼睛发亮,照著吩咐把斧子稳稳横在胸前。
“两腿分开,略宽於肩;膝盖微屈,大腿与地面平行;脚尖朝前,含胸收腹,脊背拔直。”
“这是拒马步。”薄近侯依著那二十四字口诀摆好架势,语气篤定。
顾天白已走到门口,手刚搭上门框,闻言一顿,扭过头来:“嗯,先扎马。”
薄近侯鼻尖一皱,满脸不以为然。
顾天白忍俊不禁:“练武不练功,老来一场空;练功不练腰,功夫难登高。
別嫌这马步闷,千百年来,想动拳脚,先蹲稳当——马步扎牢了,脚下才生根,对敌时才不被一撞就翻。否则別说三板斧,再玄的招式,下盘虚浮也是纸糊的架子。
你嘛,遇上个膀大腰圆的,三两下就得踉蹌跪地。”
薄近侯听不懂这些门道,咬紧牙关,硬是托著百斤巨斧蹲在那里。
顾天白閒得发慌,忽然记起前几日练过几趟、如今已有些生疏的七星连环步,便隨手捡了根枯枝,在冻土上匆匆划出北斗七宫,气沉丹田,足下生风,按著星位轨跡腾挪闪转。
约莫一炷香工夫,身上泛起热意,他收势停步,侧身一看——薄近侯早已摇摇欲坠,马步歪斜,身子前后晃荡,可那柄巨斧仍死死托在胸前,一寸未放,连喘息都压著嗓子,半分没歇。
这段时间看似短,对初学者却是最难熬的关口。
心急只会伤筋挫骨。
偏又寒风裹著湿气扑面而来,稍不留神,阴寒便顺著绷紧的筋络往里钻——轻则手脚僵麻,重则经脉滯涩,別说耍斧头,提桶水都打晃。
顾天白一步抢上前,伸手卸下巨斧,“哐当”甩在青砖地上。
薄近侯心头一紧,以为惹恼了师父,强撑著酸麻的胳膊腿想开口解释,却见顾天白反手攥住他手掌,十指交扣,旋身借力一送——“咳嘭”一声脆响,震得人耳膜嗡嗡。
还不等他回过神,顾天白手腕一收,拇指顺势沿他虎口向上疾点,合谷、列缺两穴应指而开;脚下毫不迟疑,连踏他双腿足三里、委中两处;
接著欺身贴近,右肩猛撞他怀中空门,左手翻飞如蝶,接连叩击中极、关元、石门、气海、神闕五处要穴;
最后一推一顶,借肩靠之势將他掀得离地后跃,左掌顺势滑入他臂弯,一绕一扣,四两拨千斤般轻巧一带——薄近侯整个人倏然挺直,钉在原地,纹丝不动。
说来冗长,实则电光石火。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薄近侯还懵著,像被风捲起的落叶,飘在半空没落地。
直到顾天白退开两步,他才猛然回魂,顿觉通体舒泰,毛孔张开如饮甘泉,五臟六腑熨帖得如同新蒸的软糕,方才火烧火燎的酸胀感,竟一丝不剩。
他忽然想起茶馆里说书先生拍案讲过的桥段,眼睛一亮,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替我冲开了任督二脉?”
顾天白愣住了。
这连门槛都没迈进去,別提什么调息引气的口诀了,怎么反倒冲开了任督二脉?
若真这么轻巧,满大街岂不全是踏雪无痕、摘叶飞花的宗师?
“你刚才扎马步太猛,筋骨绷得过紧,累了就该歇著再练——心急喝不了滚烫的豆腐脑,这道理都不懂?”
他抬手在薄近侯后颈一按一揉,“刚不过是替你鬆开几处滯涩的经络,免得明早浑身僵硬,连床都起不来。”
没等到自己盼著的答案,薄近侯顿时蔫了,嘴角垮下去,眉梢耷拉著,活像被秋霜扫过的嫩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