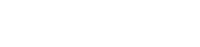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43章 惊得哑口无言
张九天与张九清飞快对视一眼,两人双修数十载,心意早已浑然一体,不必言语,只消一个眼神,便读懂彼此心底翻涌的惊疑与震动。
失踪整整三年的顾家姐弟,怎会突然现身此地?
张九天脑中浮现的,却不是三年前那些扑朔迷离的旧事,而是十多年前冬至祭天大典——那时他刚被上任掌门钦点为诵经师,第一次站在盘山祭坛之上,冷雨如丝,寒气刺骨。
满朝朱紫、江湖宿老,连那位身披明黄金袍、执掌天下的至高之人,都只能肃立承雨,不敢撑伞、不敢避让。
唯有一个六七岁的孩童,牵著那驼背异姓王的手,在仪典结束之后仰起小脸,皱眉问道:“今日为何偏要下雨?”
那位曾令庙堂震慄、江湖胆寒的老王爷,竟弯起眼角,露出从未示於外人的温软笑意,声音轻得像哄自家孙儿,连边上几位同殿称臣的老尚书都愣住了——原来这杀神也有这般絮絮叨叨的时候。
“因为天上神仙高兴,所以洒些甘霖下来。”
恰巧路过想攀谈几句的张九天,正瞧见那孩子仰头望天,小脸绷得紧紧的,气鼓鼓道:“那等我回家再下不行吗?淋湿衣裳,又要我娘费力搓洗!”
老头儿笑得更开怀了,笑声爽朗,百步之外准备启驾回宫的金袍圣人都听见了——那是他极赏识的异姓王,素来不拘形跡,此刻却笑得毫无顾忌。
倒是旁边那个扎著羊角辫的小姑娘,轻轻推了爷爷一下,细声提醒:“小些声,小些声。”
这位曾佩剑入朝、当殿骂娘的王爷,对满朝规矩不屑一顾,却偏偏把小姑娘的话听了进去,立刻“嘿嘿”两声收住笑声,脸上堆起討好的憨態,全然不顾四周同僚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半分是非,又低头问那倔强的孩子:“你倒说说,怎么让他们听你的?”
“若我有一剑在手,便叫诸天仙魔见我,尽数噤声,不敢开口。
“我若有刀在手,漫天神佛也得向我俯首弯腰。”
风雨忽敛,圜丘之上万刃无声,唯余老者朗笑震耳。
日头西斜,薄近侯掐著时辰,在小院里踱来踱去,坐立难安——终究是少年人心性,憋不住那股子焦灼,搓著手直转圈,额角沁出细汗。
屋內,顾天白正陪姐姐煮茶,抬眼瞧见薄近侯像只困在笼里的小豹子,在院子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再瞥一眼天光,估摸火候刚好,便朝姐姐頷首示意,隨即起身,牵著薄近侯出门而去。
两人一路默然,不多时到了铁匠铺。
那对讲究名字的兄弟刚收工,浑身湿透,汗珠顺著脖颈往下淌。
娄臬瘫坐在门槛上喘粗气,隨手扯了条黑黢黢的旧布抹脸;
娄圭正用同一条破布缠裹那柄巨斧,一抬眼认出来人,粗如树干的手臂猛地一抖,斧头便呼啸著旋飞而出,直奔顾天白面门!
这招看似隨意,实则暗藏机锋——斧重未明,接得轻了怕被砸个趔趄,接得重了又易失衡踉蹌。
顾天白却纹丝不动,双脚不丁不八稳扎地面,伸手一搭斧脊,顿觉沉如山岳,绝不止百斤!
右脚尖倏然点地,以左足为轴,整个人连斧带势原地旋开半圈,身形未定,手腕已翻拧如电,宣花斧在他掌中骤然腾空翻转,划出一道银亮弧光,隨后“咚”一声夯进青砖,稳如磐石。
夕照斜洒,月牙状刃口寒光迸射,斧面锻纹似流云叠涌、层层舒捲;
再看斧柄,双龙盘绕,鳞爪隱现,腾跃之势几欲破木升天,龙头迎光而立,眼瞳似有灵光流转,恍若隨时要挣脱束缚,直上九霄。
“好斧!好手艺!”顾天白脱口而出,两声“好”,字字发自肺腑,既赞这宣花巨斧浑然天成,更敬兄弟二人千锤百炼的功夫。
他全副心神都系在斧上,竟未察觉自己方才那一式四两拨千斤,已把对面两人惊得哑口无言。
娄臬心头猛跳:哥哥甩斧之力叠加斧身本重,少说一百三四十斤,偏被这眉目清俊的小哥轻巧接下,仿佛拈起一根竹杖——此人深浅,真不可测。
娄圭怔在原地,目光沉沉,半晌才回过神,嗓音微哑:“斧重一百零八斤。
斧面精钢,正面锻打九千锤,背面万锤不歇,杂质尽除。
斧柄是钨钢所铸,料是我早年存下的,煅烧整整一日夜,耐磨耐撞,放心使。”
顾天白只顾摩挲斧刃,听罢也不多问,反手將斧翻转几下,这才转向薄近侯,扬眉一笑:“来,试试。”
薄近侯早按捺不住,一听这话,箭步上前攥紧斧柄,腰马一沉,双臂发力,抡起巨斧就是三记虎啸风雷!
幸而铺子敞阔,否则这六尺长兵加上少年一身蛮劲,怕是连墙都要劈开几道裂口。
顾天白见他喜欢,顺手抓起块油布裹紧斧身,朝兄弟俩抱拳作別。
娄臬刚从顾天白那借力卸力的惊艷一招里缓过神,又被薄近侯挥斧如舞、生风似吼的架势震得张口结舌,直到两人背影消失在巷口,仍没回过神。
娄圭望著门外,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出声。
提著新得的兵器,薄近侯满心雀跃,路上便一路追问:“顾大哥,那套三招的功夫,是不是今晚就教我?”顾天白只含笑摇头:“不急,不急。”
……
酉初时分,夕阳西坠。
顾天白每日此时总有些犯晕,此刻正站在灶房门口,笨拙地拨弄柴火——从小吃惯酒楼饭馆,亲手生火做饭,对他而言比练刀还费劲。
好在早先离了铁匠铺便各自分开的薄近侯,这时拎著一只红冠昂扬的大公鸡、怀里紧紧抱著一坛寻常可见的洛神浆,小跑著回来了。
顾天白起初还有些纳闷,见他气喘吁吁却满眼亮光,顿时明白过来:这是去张罗晚饭了。
“没晚没晚!我还怕你们等不及,自己先糊弄一锅呢!”薄近侯放下酒罈,顺手拎起扑棱翅膀的公鸡,咔嚓一声扭断脖颈,咧嘴一笑,“稍等,今儿让你们开开眼——我露一手!”
话音刚落,薄近侯麻利地烧水、放血、褪毛,三下五除二就把整只鸡收拾得乾乾净净。
他抓起一把粗盐,仔仔细细抹遍鸡身里外,又拎来一捆青翠茅草,洗净后一圈圈缠紧鸡身;
接著和了一坨湿泥,厚厚糊在草衣之外。
再就著挖出的土坑垒起柴堆,把裹得严严实实的鸡团成一团搁进去,上头压满劈好的硬柴,最后“啪”地抖开火摺子,火苗“呼”地窜起。
第443章 惊得哑口无言
张九天与张九清飞快对视一眼,两人双修数十载,心意早已浑然一体,不必言语,只消一个眼神,便读懂彼此心底翻涌的惊疑与震动。
失踪整整三年的顾家姐弟,怎会突然现身此地?
张九天脑中浮现的,却不是三年前那些扑朔迷离的旧事,而是十多年前冬至祭天大典——那时他刚被上任掌门钦点为诵经师,第一次站在盘山祭坛之上,冷雨如丝,寒气刺骨。
满朝朱紫、江湖宿老,连那位身披明黄金袍、执掌天下的至高之人,都只能肃立承雨,不敢撑伞、不敢避让。
唯有一个六七岁的孩童,牵著那驼背异姓王的手,在仪典结束之后仰起小脸,皱眉问道:“今日为何偏要下雨?”
那位曾令庙堂震慄、江湖胆寒的老王爷,竟弯起眼角,露出从未示於外人的温软笑意,声音轻得像哄自家孙儿,连边上几位同殿称臣的老尚书都愣住了——原来这杀神也有这般絮絮叨叨的时候。
“因为天上神仙高兴,所以洒些甘霖下来。”
恰巧路过想攀谈几句的张九天,正瞧见那孩子仰头望天,小脸绷得紧紧的,气鼓鼓道:“那等我回家再下不行吗?淋湿衣裳,又要我娘费力搓洗!”
老头儿笑得更开怀了,笑声爽朗,百步之外准备启驾回宫的金袍圣人都听见了——那是他极赏识的异姓王,素来不拘形跡,此刻却笑得毫无顾忌。
倒是旁边那个扎著羊角辫的小姑娘,轻轻推了爷爷一下,细声提醒:“小些声,小些声。”
这位曾佩剑入朝、当殿骂娘的王爷,对满朝规矩不屑一顾,却偏偏把小姑娘的话听了进去,立刻“嘿嘿”两声收住笑声,脸上堆起討好的憨態,全然不顾四周同僚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半分是非,又低头问那倔强的孩子:“你倒说说,怎么让他们听你的?”
“若我有一剑在手,便叫诸天仙魔见我,尽数噤声,不敢开口。
“我若有刀在手,漫天神佛也得向我俯首弯腰。”
风雨忽敛,圜丘之上万刃无声,唯余老者朗笑震耳。
日头西斜,薄近侯掐著时辰,在小院里踱来踱去,坐立难安——终究是少年人心性,憋不住那股子焦灼,搓著手直转圈,额角沁出细汗。
屋內,顾天白正陪姐姐煮茶,抬眼瞧见薄近侯像只困在笼里的小豹子,在院子里兜了一圈又一圈,再瞥一眼天光,估摸火候刚好,便朝姐姐頷首示意,隨即起身,牵著薄近侯出门而去。
两人一路默然,不多时到了铁匠铺。
那对讲究名字的兄弟刚收工,浑身湿透,汗珠顺著脖颈往下淌。
娄臬瘫坐在门槛上喘粗气,隨手扯了条黑黢黢的旧布抹脸;
娄圭正用同一条破布缠裹那柄巨斧,一抬眼认出来人,粗如树干的手臂猛地一抖,斧头便呼啸著旋飞而出,直奔顾天白面门!
这招看似隨意,实则暗藏机锋——斧重未明,接得轻了怕被砸个趔趄,接得重了又易失衡踉蹌。
顾天白却纹丝不动,双脚不丁不八稳扎地面,伸手一搭斧脊,顿觉沉如山岳,绝不止百斤!
右脚尖倏然点地,以左足为轴,整个人连斧带势原地旋开半圈,身形未定,手腕已翻拧如电,宣花斧在他掌中骤然腾空翻转,划出一道银亮弧光,隨后“咚”一声夯进青砖,稳如磐石。
夕照斜洒,月牙状刃口寒光迸射,斧面锻纹似流云叠涌、层层舒捲;
再看斧柄,双龙盘绕,鳞爪隱现,腾跃之势几欲破木升天,龙头迎光而立,眼瞳似有灵光流转,恍若隨时要挣脱束缚,直上九霄。
“好斧!好手艺!”顾天白脱口而出,两声“好”,字字发自肺腑,既赞这宣花巨斧浑然天成,更敬兄弟二人千锤百炼的功夫。
他全副心神都系在斧上,竟未察觉自己方才那一式四两拨千斤,已把对面两人惊得哑口无言。
娄臬心头猛跳:哥哥甩斧之力叠加斧身本重,少说一百三四十斤,偏被这眉目清俊的小哥轻巧接下,仿佛拈起一根竹杖——此人深浅,真不可测。
娄圭怔在原地,目光沉沉,半晌才回过神,嗓音微哑:“斧重一百零八斤。
斧面精钢,正面锻打九千锤,背面万锤不歇,杂质尽除。
斧柄是钨钢所铸,料是我早年存下的,煅烧整整一日夜,耐磨耐撞,放心使。”
顾天白只顾摩挲斧刃,听罢也不多问,反手將斧翻转几下,这才转向薄近侯,扬眉一笑:“来,试试。”
薄近侯早按捺不住,一听这话,箭步上前攥紧斧柄,腰马一沉,双臂发力,抡起巨斧就是三记虎啸风雷!
幸而铺子敞阔,否则这六尺长兵加上少年一身蛮劲,怕是连墙都要劈开几道裂口。
顾天白见他喜欢,顺手抓起块油布裹紧斧身,朝兄弟俩抱拳作別。
娄臬刚从顾天白那借力卸力的惊艷一招里缓过神,又被薄近侯挥斧如舞、生风似吼的架势震得张口结舌,直到两人背影消失在巷口,仍没回过神。
娄圭望著门外,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出声。
提著新得的兵器,薄近侯满心雀跃,路上便一路追问:“顾大哥,那套三招的功夫,是不是今晚就教我?”顾天白只含笑摇头:“不急,不急。”
……
酉初时分,夕阳西坠。
顾天白每日此时总有些犯晕,此刻正站在灶房门口,笨拙地拨弄柴火——从小吃惯酒楼饭馆,亲手生火做饭,对他而言比练刀还费劲。
好在早先离了铁匠铺便各自分开的薄近侯,这时拎著一只红冠昂扬的大公鸡、怀里紧紧抱著一坛寻常可见的洛神浆,小跑著回来了。
顾天白起初还有些纳闷,见他气喘吁吁却满眼亮光,顿时明白过来:这是去张罗晚饭了。
“没晚没晚!我还怕你们等不及,自己先糊弄一锅呢!”薄近侯放下酒罈,顺手拎起扑棱翅膀的公鸡,咔嚓一声扭断脖颈,咧嘴一笑,“稍等,今儿让你们开开眼——我露一手!”
话音刚落,薄近侯麻利地烧水、放血、褪毛,三下五除二就把整只鸡收拾得乾乾净净。
他抓起一把粗盐,仔仔细细抹遍鸡身里外,又拎来一捆青翠茅草,洗净后一圈圈缠紧鸡身;
接著和了一坨湿泥,厚厚糊在草衣之外。
再就著挖出的土坑垒起柴堆,把裹得严严实实的鸡团成一团搁进去,上头压满劈好的硬柴,最后“啪”地抖开火摺子,火苗“呼”地窜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