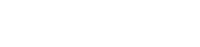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40章 內行却一眼看穿
他毫不吝嗇,拇指高高一翘,脱口而出:“龙象之力。”
薄近侯哪懂什么龙象,只咧嘴嘿嘿一笑,急切追问:“那我该练啥功夫?”
瞧著这铁塔似的少年,浑身筋骨似铜浇铁铸,倒真合了自己心中所想,顾天白点头道:“当年我大周开国大將军陈襄公陈知节,留下一套攻法。不讲繁复招式,只认一副好身板,有劲就能练。”
“劲?我管够!”薄近侯拍著自己比常人厚实一圈的肩膀,声音响亮,“我別的没有,力气堆成山!”
这举动惹得顾天白嘴角微扬,又补了一句:“这功夫也不难,就三式。”
“三式?”薄近侯一愣。虽没摸过刀剑,可也听过“燕子三抄水”“黯然九剑”这些名堂——哪门子绝学不是招式越多越显本事?怎轮到自己,就只剩三式?
顾天白看他神色,便知他肚里打什么鼓,笑道:“莫小瞧这三式。陈大將军当年便是靠它,隨天问帝踏遍南北,斩將破阵,战功赫赫。”
薄近侯半信半疑地盯著顾天白,心里直犯嘀咕:这人该不是逗自己玩吧?可转念一想,昨夜那瞎姐姐说得没错——自己除了这百十斤硬骨头,还真没什么值得骗的。
顾天白朗声一笑:“这三式当然不是死板三招,一式接一式,循环往復,连绵如江河奔涌,永无尽头。再说,功夫是皮,力气才是骨——你若能挥动七八十斤的兵刃,那威势,可就不是翻倍那么简单了。”
薄近侯將信將疑,张了张嘴又咽回去,终究还是忍不住问:“这功夫……叫啥名儿?”
“三板斧。”
“啊?”薄近侯脱口而出,满脸错愕——前头还说得云山雾罩,结果就叫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名儿?
一直静默旁观的姐姐忽然开口,语调清亮:“任他风云捲地来,三斧劈开万重霾。”
薄近侯挠著后脑勺,一脸茫然。
本就没念几天书的他,听姐姐这话反倒更懵了——这斧头,咋还劈起乾坤来了?
薄近侯当然不懂这斧法里的玄机。
且不论这路功夫的来头,当年陈知节大將军投奔开国皇帝王天问之前,本就是江湖上响噹噹的硬茬子——那会儿还是前朝大魏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草莽遍地,山头林立。
识字不过百十个的陈知节,抡著一柄六十斤重的宣花斧啸聚山林,劫豪强、济贫苦、斩恶霸,在绿林道上闯出个“铁脊樑”的名號,传得沸沸扬扬;他那套斧法,更被江湖人奉为神技,爭相摹学。
外行只瞧见斧影翻飞、呼呼作响,气势逼人,像要劈开山岳;
內行却一眼看穿,整套功夫不过三式,简练到近乎粗暴,可偏偏招招咬合如环,起承转合严丝合缝,毫无空隙可钻,任你武功再高,也难寻破绽。
后来陈知节隨天问帝南征北战、东盪西平,一路擢升至开国四大將之列,这套斧法也跟著水涨船高,被传得愈发离奇——仿佛世上无人能解、无招可破,连风过山岗都要绕著走。
其实这“三板斧”压根谈不上冠绝天下。
单论招式,唬唬寻常百姓或沙场冲阵尚可,真遇上武林中人,別说隱世不出的老怪物,便是稍有根基的门派弟子,也能从容应对;
倘若对手轻功了得、身法灵动,这斧法怕就只剩个架子,华而不实,徒惹人笑。
但话又说回来,英雄配宝刃,猛將靠神兵。
陈知节能把这三招打出威名,一大半靠的是他天生铜筋铁骨,另一大半,则全仰仗那把沉甸甸的六十斤宣花斧。
两军对垒时,他手提七尺银柄巨斧,光是那凛然杀气便足以震得敌卒胆寒;
若再不管不顾地抡开,长兵之利尽显无疑——一丈之內皆是死地,横扫竖劈,所向披靡,敌军未战先溃。
薄近侯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自天问帝立周,百年光阴流转,那些旧事早已蒙尘。他幼年家门败落,无人教他这些江湖掌故与军中秘辛,不知其中关窍,再自然不过。
“要不……咱换门功夫?这『三板斧』听著就不太牢靠。”薄近侯越琢磨越觉得虚,挠挠头,声音里透著几分羞赧。
顾天白还没开口,姐姐已忍不住“噗嗤”笑出声:“傻小子,如今满大周想拜入斧头营、苦练这三招的少年,排起来能绕皇城三圈!你可知道,天问帝开国之初,曾专设斧营操演此术,可挑来选去,竟无一人能復现陈將军当年之威——你说这是为何?”
薄近侯念书没几天,哪答得上来?但听姐姐语气,这斧法在军中竟是极受追捧。
姐姐早料到他接不住话,接著道:“就因为没人能舞得动那六十斤的宣花斧。”
薄近侯压根没听过“宣花斧”三字,只当是把大斧子;可“六十斤”三个字,他听得清清楚楚。
两军对阵,拎著六十斤的兵器廝杀,这不活脱脱是评书里说的那类顶天立地的猛將么?
姐姐自然不知他心里正浮想联翩,继续道:“將士披甲,里外加起来十八斤,再握一把六十斤的斧子,全身负重就奔七十斤去了。而这三招若离了这般分量的兵刃,哪怕顶尖高手使出来,威力也要打个对摺。你天生神力,七八十斤的斧子耍起来怕都不费劲;再配上这三记狠招,別说一个韩有鱼,来五四个,怕都近不了你的身。”
男人嘛,自古有个通病——尤其在漂亮姑娘面前,最爱硬撑面子,一听夸讚,骨头都轻三分。
姐姐这一番吹捧,连顾天白都觉得过了火,可落在薄近侯耳中,却似久旱逢甘霖,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热血直往头顶冲,恨不得当场抄斧出门,砍了韩有鱼给姨娘报仇雪恨。
他年少气盛,从没被姑娘这样夸过,十九年来头一遭,心口一热,脱口而出:“我双臂之力,千斤不止!一百斤的斧子,我也使得动!”
“我相信你行。”
撂下这句话,姐姐裙裾轻扬,转身进了屋。
薄近候当场一怔,黝黑的脸膛竟浮起一层浅淡的潮红。那句老话怎么说的?风花雪月皆可作戏,唯少年心性最是当真。他越琢磨越忍不住咧嘴傻乐。
快教我!快教我!
薄近候这股子热乎劲儿,顾天白早料到了。自家姐姐那三两句话就勾住人魂儿的本事,他见得太多——回回都像拿准了人心的脉门,轻轻一按,便叫人乖乖跟著走。
第440章 內行却一眼看穿
他毫不吝嗇,拇指高高一翘,脱口而出:“龙象之力。”
薄近侯哪懂什么龙象,只咧嘴嘿嘿一笑,急切追问:“那我该练啥功夫?”
瞧著这铁塔似的少年,浑身筋骨似铜浇铁铸,倒真合了自己心中所想,顾天白点头道:“当年我大周开国大將军陈襄公陈知节,留下一套攻法。不讲繁复招式,只认一副好身板,有劲就能练。”
“劲?我管够!”薄近侯拍著自己比常人厚实一圈的肩膀,声音响亮,“我別的没有,力气堆成山!”
这举动惹得顾天白嘴角微扬,又补了一句:“这功夫也不难,就三式。”
“三式?”薄近侯一愣。虽没摸过刀剑,可也听过“燕子三抄水”“黯然九剑”这些名堂——哪门子绝学不是招式越多越显本事?怎轮到自己,就只剩三式?
顾天白看他神色,便知他肚里打什么鼓,笑道:“莫小瞧这三式。陈大將军当年便是靠它,隨天问帝踏遍南北,斩將破阵,战功赫赫。”
薄近侯半信半疑地盯著顾天白,心里直犯嘀咕:这人该不是逗自己玩吧?可转念一想,昨夜那瞎姐姐说得没错——自己除了这百十斤硬骨头,还真没什么值得骗的。
顾天白朗声一笑:“这三式当然不是死板三招,一式接一式,循环往復,连绵如江河奔涌,永无尽头。再说,功夫是皮,力气才是骨——你若能挥动七八十斤的兵刃,那威势,可就不是翻倍那么简单了。”
薄近侯將信將疑,张了张嘴又咽回去,终究还是忍不住问:“这功夫……叫啥名儿?”
“三板斧。”
“啊?”薄近侯脱口而出,满脸错愕——前头还说得云山雾罩,结果就叫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名儿?
一直静默旁观的姐姐忽然开口,语调清亮:“任他风云捲地来,三斧劈开万重霾。”
薄近侯挠著后脑勺,一脸茫然。
本就没念几天书的他,听姐姐这话反倒更懵了——这斧头,咋还劈起乾坤来了?
薄近侯当然不懂这斧法里的玄机。
且不论这路功夫的来头,当年陈知节大將军投奔开国皇帝王天问之前,本就是江湖上响噹噹的硬茬子——那会儿还是前朝大魏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草莽遍地,山头林立。
识字不过百十个的陈知节,抡著一柄六十斤重的宣花斧啸聚山林,劫豪强、济贫苦、斩恶霸,在绿林道上闯出个“铁脊樑”的名號,传得沸沸扬扬;他那套斧法,更被江湖人奉为神技,爭相摹学。
外行只瞧见斧影翻飞、呼呼作响,气势逼人,像要劈开山岳;
內行却一眼看穿,整套功夫不过三式,简练到近乎粗暴,可偏偏招招咬合如环,起承转合严丝合缝,毫无空隙可钻,任你武功再高,也难寻破绽。
后来陈知节隨天问帝南征北战、东盪西平,一路擢升至开国四大將之列,这套斧法也跟著水涨船高,被传得愈发离奇——仿佛世上无人能解、无招可破,连风过山岗都要绕著走。
其实这“三板斧”压根谈不上冠绝天下。
单论招式,唬唬寻常百姓或沙场冲阵尚可,真遇上武林中人,別说隱世不出的老怪物,便是稍有根基的门派弟子,也能从容应对;
倘若对手轻功了得、身法灵动,这斧法怕就只剩个架子,华而不实,徒惹人笑。
但话又说回来,英雄配宝刃,猛將靠神兵。
陈知节能把这三招打出威名,一大半靠的是他天生铜筋铁骨,另一大半,则全仰仗那把沉甸甸的六十斤宣花斧。
两军对垒时,他手提七尺银柄巨斧,光是那凛然杀气便足以震得敌卒胆寒;
若再不管不顾地抡开,长兵之利尽显无疑——一丈之內皆是死地,横扫竖劈,所向披靡,敌军未战先溃。
薄近侯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自天问帝立周,百年光阴流转,那些旧事早已蒙尘。他幼年家门败落,无人教他这些江湖掌故与军中秘辛,不知其中关窍,再自然不过。
“要不……咱换门功夫?这『三板斧』听著就不太牢靠。”薄近侯越琢磨越觉得虚,挠挠头,声音里透著几分羞赧。
顾天白还没开口,姐姐已忍不住“噗嗤”笑出声:“傻小子,如今满大周想拜入斧头营、苦练这三招的少年,排起来能绕皇城三圈!你可知道,天问帝开国之初,曾专设斧营操演此术,可挑来选去,竟无一人能復现陈將军当年之威——你说这是为何?”
薄近侯念书没几天,哪答得上来?但听姐姐语气,这斧法在军中竟是极受追捧。
姐姐早料到他接不住话,接著道:“就因为没人能舞得动那六十斤的宣花斧。”
薄近侯压根没听过“宣花斧”三字,只当是把大斧子;可“六十斤”三个字,他听得清清楚楚。
两军对阵,拎著六十斤的兵器廝杀,这不活脱脱是评书里说的那类顶天立地的猛將么?
姐姐自然不知他心里正浮想联翩,继续道:“將士披甲,里外加起来十八斤,再握一把六十斤的斧子,全身负重就奔七十斤去了。而这三招若离了这般分量的兵刃,哪怕顶尖高手使出来,威力也要打个对摺。你天生神力,七八十斤的斧子耍起来怕都不费劲;再配上这三记狠招,別说一个韩有鱼,来五四个,怕都近不了你的身。”
男人嘛,自古有个通病——尤其在漂亮姑娘面前,最爱硬撑面子,一听夸讚,骨头都轻三分。
姐姐这一番吹捧,连顾天白都觉得过了火,可落在薄近侯耳中,却似久旱逢甘霖,浑身毛孔都舒展开来,热血直往头顶冲,恨不得当场抄斧出门,砍了韩有鱼给姨娘报仇雪恨。
他年少气盛,从没被姑娘这样夸过,十九年来头一遭,心口一热,脱口而出:“我双臂之力,千斤不止!一百斤的斧子,我也使得动!”
“我相信你行。”
撂下这句话,姐姐裙裾轻扬,转身进了屋。
薄近候当场一怔,黝黑的脸膛竟浮起一层浅淡的潮红。那句老话怎么说的?风花雪月皆可作戏,唯少年心性最是当真。他越琢磨越忍不住咧嘴傻乐。
快教我!快教我!
薄近候这股子热乎劲儿,顾天白早料到了。自家姐姐那三两句话就勾住人魂儿的本事,他见得太多——回回都像拿准了人心的脉门,轻轻一按,便叫人乖乖跟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