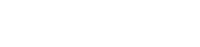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39章 谈何融会贯通?
日头升得老高,金光斜斜铺满小院时,姐姐才睁眼。
顾天白早按她习惯买回热食,刚摆好碗筷,院门就被一脚踹开——一个少年昂首阔步闯进来,布衣粗糲,肩宽腰厚,眉如墨扫、目似虎踞,浑身透著股生猛劲儿。
顾天白一怔,上下打量几回,愣是想不起这號人物打哪儿冒出来的。
姐姐却一听脚步便知来者,放下筷子,笑意浮上嘴角:“这是打算跟我弟学真功夫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顾天白这才忆起昨夜那人蓬头垢面、灯影昏黄,只记得个模糊轮廓。
此刻细看眉骨、下頜、挺直的鼻樑,才把眼前这张鲜活的脸,同昨晚那个蜷在墙角的少年严丝合缝对上。
“昨儿一夜没合眼。韩有鱼那狗东西,我翻来覆去想不出招,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信你们一回,且看看,这仇,你们究竟帮不帮得上。”
话说得硬气,字字咬得重,倒像是他施捨了天大恩惠,而非低头求人。
姐姐轻笑两声,不恼不急:“在我眼里,这法子,就是眼下最稳当的路。”
薄近侯挠挠后颈,又把那句憋了一路的话拋出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图啥?”
连顾天白都撬不开的嘴,哪轮得到他问出答案?姐姐只把话头一滑,笑吟吟道:“路上遇见,便是缘分。想帮,还非得挑个理由?”
“满大街都是人,照你这么说,你们俩天天守在街口,专等『有缘人』上门討帮衬?”薄近侯寸步不让,眼神灼灼,像要把她看穿。
“执念太重啦,小兄弟。”
姐姐笑意未减,话锋却忽地一转,“你要雪恨,我们能助你雪恨——还管它天高地厚、前因后果作甚?男子汉做事,该断则断,该行则行。你这般犹犹豫豫、磨磨唧唧,连我都嫌你拖沓。”
记住我们101看书网
一番话夹枪带棒,薄近侯脸上顿时烧了起来,黝黑麵皮底下,悄悄漫开一层暗红。
“那你说,怎么才能在几天之內让我把功夫练出点模样?”薄近侯见嘴上斗不过这双目失明的姑娘,乾脆收住话头,另起炉灶。
“这事儿你得问我家弟弟。”姐姐朝顾天白扬了扬下巴,“他最懂。”
顾天白昨夜一听姐姐要把教功夫的差事塞给自己,脑袋就嗡嗡作响;今早薄近侯真登了门,他更觉这活儿烫手得能燎起泡来。
习武哪是灌一勺蜜就能甜到心尖上的事?
全是从小扎根基、日日磨筋骨的苦功。
招式要反覆锤炼,劲力要千锤百炼,再灵透些的,还得在熟极而流里撞出自己的门道,才算摸著大道的边儿。
一招一式没个七八年浸润,谈何融会贯通?
自己若真去教,薄近侯早已过了打底子的黄金年纪,偏还张口就要速成——这不是逼人一口吞下整只烤全羊,连骨头都不吐?
他低头小口啜著餶飿面,脑中飞转:先稳住薄近侯,好让姐姐从自己吹出去的牛皮里体面抽身。
见对方目光扫过来,他眼珠一溜,搁下碗筷,抬手朝院角那堆房主撂下的硬木一指:“去,先把柴劈了。”
薄近侯一怔。他虽没正经练过武,可常年走南闯北拉货,耳濡目染也听过不少——什么马步蹲得腿打颤、拳脚打出火星子,才是入门正道。可谁提过劈柴是头一课?
他眼睛瞪得溜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你不是教我功夫?让我劈柴算哪门子道理?”
“先掂掂你身上有没有那股子练武的劲儿。”顾天白这话刚出口,自己都差点信了。
薄近侯到底没摸过门道,听他这么一说,竟觉得挺有分量,二话不说擼起袖管,大步朝木堆走去。
院外斧声咚咚响起,姐姐终於憋不住,噗嗤笑出声,指尖点著顾天白,又气又笑:“你呀你,实在不会教,直说就是了,我还能不替你兜著?倒好,让人家抡斧头去了——难不成真打算让他劈到立夏?”
顾天白脸上微热,忙摆手:“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话音里带了点虚浮的敷衍。
薄近侯確实有一身蛮劲,这是顾天白第一眼就咂摸出来的。
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掌厚的榆木墩子,寻常人怕得劈三五下才见裂痕,他却利落得很:斧起斧落,咔嚓一声,木屑四溅,盏茶工夫,劈出的柴够姐弟俩烧上小一个月。
见顾天白目光停在自己身上,薄近侯索性加了把劲,劈得更起劲。顾天白正绞尽脑汁搜刮招式,他已由一劈二、二劈四、四劈八,身边又堆起一座小山。
正月初的晨风还裹著刺骨凉意,薄近侯却劈得额角沁汗,存心显摆,忽地旋腕抖斧,“嗖”地一甩,斧柄绕腕翻了个花,末了“咚”一声,稳稳钉进面前圆木,斧刃入木三分,纹丝不动。
这近乎本能的一手,却像根火摺子,“啪”地点燃了顾天白脑中一团混沌——他猛地抬头,脱口而出:“小时候劈过柴?”
薄近侯用袖子抹了把汗,蹲到顾天白对面,声音低了些:“跟著姨娘討饭那阵子,我就靠劈柴换几文钱。”话音未落,眼神便沉了下去,像被风吹暗的烛火。
顾天白看得分明——那点子黯然不是装的。相依为命的姨娘说走就走,他不过是个半大孩子,心里发空,嘴上难言。劝的话堵在喉咙里,最后只挤出一句:“你力气,到底有多大?”
“大得很!”薄近侯本就爱动爱闹,被这一激,顿时来了神,目光扫过小院,一眼锁住墙角那块蒙尘的旧磨盘。
磨盘不大,斜倚在墙根,石面磨得油亮,少说也转了二十年光景。青石质地,沉甸甸的,估摸著不下百斤。薄近侯没多想,挽起袖子就走了过去。
挽起袖口凑近磨盘,裸露的手臂泛著经年日晒雨淋淬炼出的铁锈色光泽。
他稳稳立在磨盘边,双腿如生根般扎进泥土,双臂环住那五尺多高的石盘,膝盖微沉、腰背绷紧,喉头一滚,低吼出声“哈!”——手背上青筋暴突如虬枝盘绕,脚下泥地竟簌簌震颤,陷下浅浅一圈印痕。
磨盘纹丝不动。
薄近侯也纹丝不动。
黝黑面庞渐渐涨成酱紫,胳膊上血管如活蛇般扭动著爬向颈侧,额角隨即暴起粗壮扭曲的筋络,青白交杂,触目惊心。
“呃啊——!”
又是一声闷雷似的嘶吼,空气仿佛被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沉滯得令人耳膜发胀。
连顾天白这等见过血、闯过阵的老江湖,胸口都像压了块冷铁,呼吸为之一滯。
那百十斤重的石磨盘久置荒原,底座早已与泥地长死,浮土板结如铁壳。
隨著薄近侯力道层层加压,表层硬壳终於咔咔龟裂,簌簌剥落,石盘边缘缓缓翘起,肉眼可见地离地抬升——而他双脚却越陷越深,脚踝几乎没入土中,足见那股蛮劲有多骇人。
石盘刚离地一掌宽,薄近侯便抬脚转身。动作迟缓得如同拨动沉重齿轮,一步一顿,停顿再启,活像泥沼里拖著身子挪动的巨兽。
就这么一个转身,他竟挪了六步才斜斜侧过身,目光直直投向顾天白。
鬆手剎那,“哐啷”一声砸响,惊得旁边出神的姐姐猛然一抖,薄近侯挠头咧嘴,憨笑得有点傻气。
他粗喘几口,拍拍手掌抖落尘土,气息渐匀,脸上紫红慢慢退潮,眼里却亮著光:“咋样?”
顾天白早听闻过“扛鼎裂碑”的异士传说,可耳听终是虚,眼见才为实。
眼前这少年单凭一股蛮劲便撼动磐石,心头不由暗赞一声硬扎,这般膂力,放眼整个大周,怕也数不出几个。
第439章 谈何融会贯通?
日头升得老高,金光斜斜铺满小院时,姐姐才睁眼。
顾天白早按她习惯买回热食,刚摆好碗筷,院门就被一脚踹开——一个少年昂首阔步闯进来,布衣粗糲,肩宽腰厚,眉如墨扫、目似虎踞,浑身透著股生猛劲儿。
顾天白一怔,上下打量几回,愣是想不起这號人物打哪儿冒出来的。
姐姐却一听脚步便知来者,放下筷子,笑意浮上嘴角:“这是打算跟我弟学真功夫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顾天白这才忆起昨夜那人蓬头垢面、灯影昏黄,只记得个模糊轮廓。
此刻细看眉骨、下頜、挺直的鼻樑,才把眼前这张鲜活的脸,同昨晚那个蜷在墙角的少年严丝合缝对上。
“昨儿一夜没合眼。韩有鱼那狗东西,我翻来覆去想不出招,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信你们一回,且看看,这仇,你们究竟帮不帮得上。”
话说得硬气,字字咬得重,倒像是他施捨了天大恩惠,而非低头求人。
姐姐轻笑两声,不恼不急:“在我眼里,这法子,就是眼下最稳当的路。”
薄近侯挠挠后颈,又把那句憋了一路的话拋出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图啥?”
连顾天白都撬不开的嘴,哪轮得到他问出答案?姐姐只把话头一滑,笑吟吟道:“路上遇见,便是缘分。想帮,还非得挑个理由?”
“满大街都是人,照你这么说,你们俩天天守在街口,专等『有缘人』上门討帮衬?”薄近侯寸步不让,眼神灼灼,像要把她看穿。
“执念太重啦,小兄弟。”
姐姐笑意未减,话锋却忽地一转,“你要雪恨,我们能助你雪恨——还管它天高地厚、前因后果作甚?男子汉做事,该断则断,该行则行。你这般犹犹豫豫、磨磨唧唧,连我都嫌你拖沓。”
记住我们101看书网
一番话夹枪带棒,薄近侯脸上顿时烧了起来,黝黑麵皮底下,悄悄漫开一层暗红。
“那你说,怎么才能在几天之內让我把功夫练出点模样?”薄近侯见嘴上斗不过这双目失明的姑娘,乾脆收住话头,另起炉灶。
“这事儿你得问我家弟弟。”姐姐朝顾天白扬了扬下巴,“他最懂。”
顾天白昨夜一听姐姐要把教功夫的差事塞给自己,脑袋就嗡嗡作响;今早薄近侯真登了门,他更觉这活儿烫手得能燎起泡来。
习武哪是灌一勺蜜就能甜到心尖上的事?
全是从小扎根基、日日磨筋骨的苦功。
招式要反覆锤炼,劲力要千锤百炼,再灵透些的,还得在熟极而流里撞出自己的门道,才算摸著大道的边儿。
一招一式没个七八年浸润,谈何融会贯通?
自己若真去教,薄近侯早已过了打底子的黄金年纪,偏还张口就要速成——这不是逼人一口吞下整只烤全羊,连骨头都不吐?
他低头小口啜著餶飿面,脑中飞转:先稳住薄近侯,好让姐姐从自己吹出去的牛皮里体面抽身。
见对方目光扫过来,他眼珠一溜,搁下碗筷,抬手朝院角那堆房主撂下的硬木一指:“去,先把柴劈了。”
薄近侯一怔。他虽没正经练过武,可常年走南闯北拉货,耳濡目染也听过不少——什么马步蹲得腿打颤、拳脚打出火星子,才是入门正道。可谁提过劈柴是头一课?
他眼睛瞪得溜圆,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你不是教我功夫?让我劈柴算哪门子道理?”
“先掂掂你身上有没有那股子练武的劲儿。”顾天白这话刚出口,自己都差点信了。
薄近侯到底没摸过门道,听他这么一说,竟觉得挺有分量,二话不说擼起袖管,大步朝木堆走去。
院外斧声咚咚响起,姐姐终於憋不住,噗嗤笑出声,指尖点著顾天白,又气又笑:“你呀你,实在不会教,直说就是了,我还能不替你兜著?倒好,让人家抡斧头去了——难不成真打算让他劈到立夏?”
顾天白脸上微热,忙摆手:“看看再说,看看再说。”话音里带了点虚浮的敷衍。
薄近侯確实有一身蛮劲,这是顾天白第一眼就咂摸出来的。
十七八岁的少年,一掌厚的榆木墩子,寻常人怕得劈三五下才见裂痕,他却利落得很:斧起斧落,咔嚓一声,木屑四溅,盏茶工夫,劈出的柴够姐弟俩烧上小一个月。
见顾天白目光停在自己身上,薄近侯索性加了把劲,劈得更起劲。顾天白正绞尽脑汁搜刮招式,他已由一劈二、二劈四、四劈八,身边又堆起一座小山。
正月初的晨风还裹著刺骨凉意,薄近侯却劈得额角沁汗,存心显摆,忽地旋腕抖斧,“嗖”地一甩,斧柄绕腕翻了个花,末了“咚”一声,稳稳钉进面前圆木,斧刃入木三分,纹丝不动。
这近乎本能的一手,却像根火摺子,“啪”地点燃了顾天白脑中一团混沌——他猛地抬头,脱口而出:“小时候劈过柴?”
薄近侯用袖子抹了把汗,蹲到顾天白对面,声音低了些:“跟著姨娘討饭那阵子,我就靠劈柴换几文钱。”话音未落,眼神便沉了下去,像被风吹暗的烛火。
顾天白看得分明——那点子黯然不是装的。相依为命的姨娘说走就走,他不过是个半大孩子,心里发空,嘴上难言。劝的话堵在喉咙里,最后只挤出一句:“你力气,到底有多大?”
“大得很!”薄近侯本就爱动爱闹,被这一激,顿时来了神,目光扫过小院,一眼锁住墙角那块蒙尘的旧磨盘。
磨盘不大,斜倚在墙根,石面磨得油亮,少说也转了二十年光景。青石质地,沉甸甸的,估摸著不下百斤。薄近侯没多想,挽起袖子就走了过去。
挽起袖口凑近磨盘,裸露的手臂泛著经年日晒雨淋淬炼出的铁锈色光泽。
他稳稳立在磨盘边,双腿如生根般扎进泥土,双臂环住那五尺多高的石盘,膝盖微沉、腰背绷紧,喉头一滚,低吼出声“哈!”——手背上青筋暴突如虬枝盘绕,脚下泥地竟簌簌震颤,陷下浅浅一圈印痕。
磨盘纹丝不动。
薄近侯也纹丝不动。
黝黑面庞渐渐涨成酱紫,胳膊上血管如活蛇般扭动著爬向颈侧,额角隨即暴起粗壮扭曲的筋络,青白交杂,触目惊心。
“呃啊——!”
又是一声闷雷似的嘶吼,空气仿佛被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沉滯得令人耳膜发胀。
连顾天白这等见过血、闯过阵的老江湖,胸口都像压了块冷铁,呼吸为之一滯。
那百十斤重的石磨盘久置荒原,底座早已与泥地长死,浮土板结如铁壳。
隨著薄近侯力道层层加压,表层硬壳终於咔咔龟裂,簌簌剥落,石盘边缘缓缓翘起,肉眼可见地离地抬升——而他双脚却越陷越深,脚踝几乎没入土中,足见那股蛮劲有多骇人。
石盘刚离地一掌宽,薄近侯便抬脚转身。动作迟缓得如同拨动沉重齿轮,一步一顿,停顿再启,活像泥沼里拖著身子挪动的巨兽。
就这么一个转身,他竟挪了六步才斜斜侧过身,目光直直投向顾天白。
鬆手剎那,“哐啷”一声砸响,惊得旁边出神的姐姐猛然一抖,薄近侯挠头咧嘴,憨笑得有点傻气。
他粗喘几口,拍拍手掌抖落尘土,气息渐匀,脸上紫红慢慢退潮,眼里却亮著光:“咋样?”
顾天白早听闻过“扛鼎裂碑”的异士传说,可耳听终是虚,眼见才为实。
眼前这少年单凭一股蛮劲便撼动磐石,心头不由暗赞一声硬扎,这般膂力,放眼整个大周,怕也数不出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