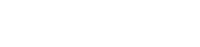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48章 登门授艺的师父
“嘖,底子真不赖。”顾天白低低一嘆。
他几步踱到薄近候身后,俯身探手,指尖精准扣住颈后大椎穴,隨即掌心发力,自上而下连击身柱、灵台、中枢、悬枢、命门、阳关六处要穴;
再反手由腰背向上轻抚数遍,指腹温热贴著脊线游走,直到单衣下那截脊骨微微发烫、透出暖意,才收势退开。
再抬眼望去——薄近候仍闭目端坐,可这腊月清晨的冷气里,他头顶竟浮起一缕淡青薄雾,如丝如缕,盘旋升腾,仿佛活物般缓缓呼吸。
“五气朝元?”顾天白眉峰微蹙,心头一震。这异象他只在幼时翻烂的一本脆皮旧册里瞥见过——纸页泛黄酥脆,稍一用力便簌簌掉渣,书名早被虫蛀得只剩半角残影。
书中说,五气即心肝脾肺肾所藏之神、魂、意、魄、精,先天本具礼、仁、信、义、智之性;及至后天,识神初动,游魂渐扰,妄意横生,鬼魄暗涌,浊精淤滯——待五行火木土金水归位调和,方能涤尽七情六慾,返照本元。
当年他缠著无数人追问,无人答得上来,唯有一个早已杳无音信的老拳师,叼著菸斗含糊道:“怕是失传百年的真功夫,骨头缝里长出来的。”
顾天白甩甩头,想把这荒唐念头抖落乾净。
可那缕青雾仍在薄近侯头顶悠悠打转,像无声的嘲弄。
薄近候双目紧闭,自然不知自己头顶正腾云驾雾;
就算睁眼,也瞧不见这奇景。他只觉通体鬆快,比昨夜那顿噼里啪啦的拍打更透彻——仿佛有条温热小蛇,从后脑勺一路滑下,钻进肩颈,缠过腰胯,游遍四肢百骸。
绕第一圈,筋骨舒展;第二圈,酥麻如蚁爬;第三圈,痒得人脚趾蜷缩,恨不得挠穿皮肉才痛快。
顾天白屏息静立,不敢惊扰;薄近候沉溺其中,不愿抽身。一个负手而立如松,一个盘膝而坐似钟,两人在微光里僵成两尊泥塑。从天边泛青,到雄鸡三唱,再到日头跃出屋檐——若非姐姐推门声刺破院中凝滯的寂静,怕是连风都捨不得吹动他们衣角。
“天白?今儿怎么没来?”姐姐摸索著踏出院门,声音里满是纳闷。往常这时候,弟弟早该攥著帕子等在门口,替她系襟带、绞热巾了。
“没事,教近候练桩呢。”顾天白嘴角一扬,语调轻快得像在说“今早粥熬得稠”,半点不露异样。
姐姐听不出破绽,转身回屋。顾天白再看薄近候,只见他面颊润泽泛光,朝阳斜斜镀在脸上,竟映出婴儿肌肤般的柔光——那层常年晒出的黝黑硬壳悄然软化,底下透出新生嫩肉的微粉。
“有啥动静没?”顾天白问。
“嗯……”薄近候喉结滚动,飞快扫了眼紧闭的屋门,耳根发烫,凑近顾天白压低嗓子:“我……想解手。”
顾天白先是一怔,旋即心领神会——那缕青雾,怕是把十年积攒的浊气全蒸腾出去了。眼下腹中鼓胀,正是臟腑清空、经络重铸的徵兆。这小子哪是练武,分明是撞开了易筋洗髓的门缝,连门槛都没跨,直接滚进了內家真境。
目送薄近候拔腿冲向茅房,顾天白忽觉喉咙发乾。翻遍古今天下武谱,他还真没见过谁劈柴劈著劈著,就劈出个脱胎换骨来。
此子绝非池中物,遇雨则腾,遇风则化。
可下一刻,顾天白抄起宣花巨斧往薄近侯手里一塞:“左右各劈一百记!”
薄近候当场愣住,斧柄差点脱手。
这到底啥时候才算入门?昨日说“得有趁手傢伙”,结果等锻刀等了一整天;刀没见著,先劈了一宿柴;夜里刚蹲完马步,今儿倒好,让他对著空气抡斧头。莫非劈完左右,还得上下各一百?上下完了再前后?再前后完了,是不是得原地打滚三百圈?
他越想越焦,斧刃在晨光里晃得刺眼——怕就怕自己这股子火气还没烧旺,早被这没头苍蝇似的折腾,给浇得只剩一缕青烟了。
薄近侯握斧的手鬆松垮垮,斧刃歪斜,眼神飘忽,顾天白一眼就瞧出他心不在焉。
这神情,活脱脱就是当年自己初学武时的模样——那些登门授艺的师父,哪个不是先端足架子、吊足胃口?
有人把人胃口吊得滚烫,转头却推说“火候未到”“根基不稳”,拖著不教真章;
后来才明白,多半是衝著自家老爷子开出的厚酬来的江湖油子,嘴上功夫了得,手上全是虚招。
可那时的自己,不也是一腔热忱,渐渐被磨得蔫头耷脑?
“认真些,挥满二百下,斧子便如长在你手上一般顺手,往后学招,自然势如破竹。”
薄近侯一听,只觉这话轻飘飘的,像拿团棉花塞耳朵,敷衍得连余味都不留。
顾天白暗自莞尔,不再多劝,抬眼扫过小院,径直走向墙角,抄起房东扔在那儿的一把旧锄头,道:“来,照我样子做。”
薄近侯眼睛倏地亮了,立刻收神敛气,站得笔直,目不转睛盯紧顾天白一举一动。
顾天白腰胯一沉,马步扎稳,以锄代斧,朗声道:“三板斧,名副其实,就三式。第一式——劈脑袋!”
话音未落,他身形暴起,锄头裹著风声自顶门直贯而下,势如雷劈枯木,又狠又准。
“第二式——鬼剃头!”
锄锋劈至半途骤然剎住,腕子一拧,锄身斜挑而上,快得只留下一道青灰残影。
“第三式——掏耳朵!”
锄头掠至齐胸高处,他手腕猛然翻转下压,锄杆横扫,身子旋开,弯腰绕顶一圈,如环抱苍穹,再挺身而立,目光灼灼望向薄近侯。
薄近侯仍睁大双眼,怔怔盯著他,半信半疑:“这就……完了?”
顾天白頷首。
薄近侯犹不甘心,又追问一句:“真没了?”
顾天白仍点头。
“这也太寻常了吧!”薄近侯撇嘴,“没这几个花哨名字,我抡锄头也能这么来!”
顾天白不置可否。
当年他初见那本薄得可怜、勉强能称作秘籍的册子时,脸上也是这般错愕。
倒是封皮上三个大字“三板斧”,写得极有神采——铁画银鉤,一气呵成,刚劲中透著桀驁,笔锋断而不散,余势缠绵,仿佛能从中窥见那位开国猛將陈知节横刀立马、睥睨天下的豪气。
可除此以外,再无半分亮眼之处。全书不过七八页,其中六页都在讲陈知节——从襁褓啼哭到病榻咽气,事无巨细;
武功渊源更是吹得云山雾罩,若非末页赫然印著撰者姓名,顾天白几乎要以为是陈知节自己僱人代笔、夸耀功业的自传。
后来才听说,那位力拔山兮、万人辟易的大將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是硬塞银子请人捉刀写的。
即便如此,最后两页寥寥数招图解,顾天白反覆揣摩后,仍不得不嘆服:三式衔接如江河奔涌,环环相扣,浑然天成,毫无滯涩。
別小看薄近侯嘴上说的“没名字我也使得出来”——那些看似田间地头刨土翻泥的动作,一旦连成一线、贯入呼吸,衝锋陷阵时,便是百人难近其身。
书里还提过,陈知节隨先皇平定天下后,曾专程请来一位外家拳高手,教他吐纳导引之术。
自此,三板斧威力倍增——气息一通,斧影翻飞,酣战半个时辰亦不喘不颤,端的是玄妙非常。
这些话,顾天白懒得对薄近侯细讲。那些玄而又玄的门道,听在他耳里,怕比听天书还费劲。
第448章 登门授艺的师父
“嘖,底子真不赖。”顾天白低低一嘆。
他几步踱到薄近候身后,俯身探手,指尖精准扣住颈后大椎穴,隨即掌心发力,自上而下连击身柱、灵台、中枢、悬枢、命门、阳关六处要穴;
再反手由腰背向上轻抚数遍,指腹温热贴著脊线游走,直到单衣下那截脊骨微微发烫、透出暖意,才收势退开。
再抬眼望去——薄近候仍闭目端坐,可这腊月清晨的冷气里,他头顶竟浮起一缕淡青薄雾,如丝如缕,盘旋升腾,仿佛活物般缓缓呼吸。
“五气朝元?”顾天白眉峰微蹙,心头一震。这异象他只在幼时翻烂的一本脆皮旧册里瞥见过——纸页泛黄酥脆,稍一用力便簌簌掉渣,书名早被虫蛀得只剩半角残影。
书中说,五气即心肝脾肺肾所藏之神、魂、意、魄、精,先天本具礼、仁、信、义、智之性;及至后天,识神初动,游魂渐扰,妄意横生,鬼魄暗涌,浊精淤滯——待五行火木土金水归位调和,方能涤尽七情六慾,返照本元。
当年他缠著无数人追问,无人答得上来,唯有一个早已杳无音信的老拳师,叼著菸斗含糊道:“怕是失传百年的真功夫,骨头缝里长出来的。”
顾天白甩甩头,想把这荒唐念头抖落乾净。
可那缕青雾仍在薄近侯头顶悠悠打转,像无声的嘲弄。
薄近候双目紧闭,自然不知自己头顶正腾云驾雾;
就算睁眼,也瞧不见这奇景。他只觉通体鬆快,比昨夜那顿噼里啪啦的拍打更透彻——仿佛有条温热小蛇,从后脑勺一路滑下,钻进肩颈,缠过腰胯,游遍四肢百骸。
绕第一圈,筋骨舒展;第二圈,酥麻如蚁爬;第三圈,痒得人脚趾蜷缩,恨不得挠穿皮肉才痛快。
顾天白屏息静立,不敢惊扰;薄近候沉溺其中,不愿抽身。一个负手而立如松,一个盘膝而坐似钟,两人在微光里僵成两尊泥塑。从天边泛青,到雄鸡三唱,再到日头跃出屋檐——若非姐姐推门声刺破院中凝滯的寂静,怕是连风都捨不得吹动他们衣角。
“天白?今儿怎么没来?”姐姐摸索著踏出院门,声音里满是纳闷。往常这时候,弟弟早该攥著帕子等在门口,替她系襟带、绞热巾了。
“没事,教近候练桩呢。”顾天白嘴角一扬,语调轻快得像在说“今早粥熬得稠”,半点不露异样。
姐姐听不出破绽,转身回屋。顾天白再看薄近候,只见他面颊润泽泛光,朝阳斜斜镀在脸上,竟映出婴儿肌肤般的柔光——那层常年晒出的黝黑硬壳悄然软化,底下透出新生嫩肉的微粉。
“有啥动静没?”顾天白问。
“嗯……”薄近候喉结滚动,飞快扫了眼紧闭的屋门,耳根发烫,凑近顾天白压低嗓子:“我……想解手。”
顾天白先是一怔,旋即心领神会——那缕青雾,怕是把十年积攒的浊气全蒸腾出去了。眼下腹中鼓胀,正是臟腑清空、经络重铸的徵兆。这小子哪是练武,分明是撞开了易筋洗髓的门缝,连门槛都没跨,直接滚进了內家真境。
目送薄近候拔腿冲向茅房,顾天白忽觉喉咙发乾。翻遍古今天下武谱,他还真没见过谁劈柴劈著劈著,就劈出个脱胎换骨来。
此子绝非池中物,遇雨则腾,遇风则化。
可下一刻,顾天白抄起宣花巨斧往薄近侯手里一塞:“左右各劈一百记!”
薄近候当场愣住,斧柄差点脱手。
这到底啥时候才算入门?昨日说“得有趁手傢伙”,结果等锻刀等了一整天;刀没见著,先劈了一宿柴;夜里刚蹲完马步,今儿倒好,让他对著空气抡斧头。莫非劈完左右,还得上下各一百?上下完了再前后?再前后完了,是不是得原地打滚三百圈?
他越想越焦,斧刃在晨光里晃得刺眼——怕就怕自己这股子火气还没烧旺,早被这没头苍蝇似的折腾,给浇得只剩一缕青烟了。
薄近侯握斧的手鬆松垮垮,斧刃歪斜,眼神飘忽,顾天白一眼就瞧出他心不在焉。
这神情,活脱脱就是当年自己初学武时的模样——那些登门授艺的师父,哪个不是先端足架子、吊足胃口?
有人把人胃口吊得滚烫,转头却推说“火候未到”“根基不稳”,拖著不教真章;
后来才明白,多半是衝著自家老爷子开出的厚酬来的江湖油子,嘴上功夫了得,手上全是虚招。
可那时的自己,不也是一腔热忱,渐渐被磨得蔫头耷脑?
“认真些,挥满二百下,斧子便如长在你手上一般顺手,往后学招,自然势如破竹。”
薄近侯一听,只觉这话轻飘飘的,像拿团棉花塞耳朵,敷衍得连余味都不留。
顾天白暗自莞尔,不再多劝,抬眼扫过小院,径直走向墙角,抄起房东扔在那儿的一把旧锄头,道:“来,照我样子做。”
薄近侯眼睛倏地亮了,立刻收神敛气,站得笔直,目不转睛盯紧顾天白一举一动。
顾天白腰胯一沉,马步扎稳,以锄代斧,朗声道:“三板斧,名副其实,就三式。第一式——劈脑袋!”
话音未落,他身形暴起,锄头裹著风声自顶门直贯而下,势如雷劈枯木,又狠又准。
“第二式——鬼剃头!”
锄锋劈至半途骤然剎住,腕子一拧,锄身斜挑而上,快得只留下一道青灰残影。
“第三式——掏耳朵!”
锄头掠至齐胸高处,他手腕猛然翻转下压,锄杆横扫,身子旋开,弯腰绕顶一圈,如环抱苍穹,再挺身而立,目光灼灼望向薄近侯。
薄近侯仍睁大双眼,怔怔盯著他,半信半疑:“这就……完了?”
顾天白頷首。
薄近侯犹不甘心,又追问一句:“真没了?”
顾天白仍点头。
“这也太寻常了吧!”薄近侯撇嘴,“没这几个花哨名字,我抡锄头也能这么来!”
顾天白不置可否。
当年他初见那本薄得可怜、勉强能称作秘籍的册子时,脸上也是这般错愕。
倒是封皮上三个大字“三板斧”,写得极有神采——铁画银鉤,一气呵成,刚劲中透著桀驁,笔锋断而不散,余势缠绵,仿佛能从中窥见那位开国猛將陈知节横刀立马、睥睨天下的豪气。
可除此以外,再无半分亮眼之处。全书不过七八页,其中六页都在讲陈知节——从襁褓啼哭到病榻咽气,事无巨细;
武功渊源更是吹得云山雾罩,若非末页赫然印著撰者姓名,顾天白几乎要以为是陈知节自己僱人代笔、夸耀功业的自传。
后来才听说,那位力拔山兮、万人辟易的大將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是硬塞银子请人捉刀写的。
即便如此,最后两页寥寥数招图解,顾天白反覆揣摩后,仍不得不嘆服:三式衔接如江河奔涌,环环相扣,浑然天成,毫无滯涩。
別小看薄近侯嘴上说的“没名字我也使得出来”——那些看似田间地头刨土翻泥的动作,一旦连成一线、贯入呼吸,衝锋陷阵时,便是百人难近其身。
书里还提过,陈知节隨先皇平定天下后,曾专程请来一位外家拳高手,教他吐纳导引之术。
自此,三板斧威力倍增——气息一通,斧影翻飞,酣战半个时辰亦不喘不颤,端的是玄妙非常。
这些话,顾天白懒得对薄近侯细讲。那些玄而又玄的门道,听在他耳里,怕比听天书还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