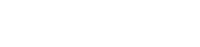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42章 有过一场硬碰硬
“要宣花斧。”顾天白补了一句。
娄圭眼神一顿,眸中疑云顿起。宣花斧?名头听著寻常,实则不是谁都能掂量的硬茬。
“打得出来?”顾天白再问。
娄圭目光扫过眼前这个比自己矮了一尺有余、面容清朗的青年,略一沉吟:“手边正好有块上好铁胚,申时来取,绝不误事。”他顿了顿,又问,“多重?”
“你能锻多重,我就用多重。”
满屋静了半拍。
顾天白先是一怔,隨即摇头苦笑;兄弟俩互看一眼,终於憋不住,噗嗤笑出声。
乾坤岂容狂徒立,敢摘星斗掷沧溟。
终究是少年心性。
薄近候却不管这些,张口就来一句,直把娄圭兄弟笑得前仰后合。
娄臬毫不客气,当场呛声:“我哥能打出百斤重的,你扛得动?!”
“你们锻得出来,我就扛得动。”薄近侯挺直腰杆,寸步不让,可那副绷紧脖颈、咬牙瞪眼的模样,在打铁兄弟眼里,倒像小孩儿赌气,倔得有点可爱。
“这兵刃费工是费工,却不算多难。今儿头一桩买卖,咱们图个吉利,让些利,整数一百两——定金先交一半。”
娄圭不像娄臬那般爱较劲,许是年长几岁,早明白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瞧他膀大腰圆、满脸煤灰,心却细如髮丝。
他怕顾天白二人拿自己寻开心,前前后后盘算得滴水不漏,连退路都悄悄留好了。
“一百两?你不如去府衙抢库银!”顾天白从小不把银钱当回事,这百两雪花银,够寻常三口之家吃穿嚼用六七年,於他不过帐本上一个墨点;
薄近侯却当场跳脚,仿佛对方不是做生意,而是抡著斧子拦路劫道。
“嫌贵?请便,门在那边。”娄臬嘴角一翘,神气活现,活像刚贏了场斗鸡——他和薄近侯年纪相仿,话赶话呛几句,倒像比谁嗓门更亮、谁脸皮更厚,输贏全写在脸上。
这话他確实说得硬气:歷下城里,別说找第二家能打利刃的铺子,就是百里之內,怕也寻不出第三处炉火通红的铁匠铺。
薄近侯一时语塞,手指抠著衣角,急得直挠后脑勺,嘴张了又合,愣是没挤出半个字来。
“只要东西扎实,价钱高低倒不打紧。”顾天白边说边摸出一张银票,手刚抬起来,却被薄近侯一把攥住手腕。
薄近侯心眼实在,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
在他看来,拜师得敬束脩,就像城里私塾里的学子,逢年过节拎著五花肉、提著老烧酒往先生家钻。
顾天白教他功夫,从没提过一个铜板,他早觉得这份情义重过千斤;如今再让他掏人家的钱买兵器?
他寧愿赤手空拳去劈柴,也不肯点头。
可对方这价码,真真是狮子甩尾——他给宋家跑腿送货三年,一年拢共才挣十几二十两;別说一百两,光那五十两定金,他翻遍所有口袋、借遍左邻右舍,也凑不出半文。
“怎么?”顾天白一怔,完全没料到他心里转著这许多念头。
“我……我自己来。”薄近侯声音发虚,话还没落地,耳根子就烫了起来。
顾天白目光一扫,心里顿时透亮:这傻小子正为钱发愁呢。他唇角微扬,语气轻快:“我先垫上,事成之后你再还我,乾净利落。”
话说得云淡风轻,薄近侯再憨也听明白了——这是替他兜著底,护著他那点可怜的面子,免得在外人面前露怯丟份。
有时一句话,暖得人骨头缝都酥;有时一句话,冷得人脊梁骨发僵。
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六月寒。
这哪是什么权术?不过是常年跟著姐姐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举手投足已沾上几分她的分寸与体谅。
娄臬接过银票,手竟微微发颤。
他这辈子头回摸著这么厚实的票子,反反覆覆对光瞧、指腹捻、对著窗缝吹气验——不是没见过世面,倒像是生怕它眨眼化作纸灰。
顾天白神色坦然:“钱一次结清,不必分什么定金尾款,麻烦。”
娄圭却突然抱拳躬身,声调也沉了几分:“敢问尊姓大名?”——这是进门以来,他头一回露出几分敬意。在他眼里,整个歷下城,能甩出百两银票还不眨一下眼的,掰著指头都数不满五人;
可眼前这张脸,他確確实实没见过。
顾天白这些年隨姐姐辗转奔走,反倒是在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歷下城里,被人频频问起名號。
若非这几日接连被问,他倒真想把那个让大周朝野听见就屏息噤声的姓氏,悄悄抹去。
“我住县南巷,先前在天然居落脚过些日子。若信不过这票子,尽可去天然居寻老板,他认得我,也知我落脚处。”顾天白答得乾脆,娄圭却猛地睁大双眼:“原来是你!”
“认得我?”顾天白微讶,旋即一笑——前几日那场风波,早传遍大街小巷,此刻听见这声惊呼,倒也不奇怪了。
娄臬手指直戳顾天白,舌头打结似的,“你……你不是那个……把杨家女婿揍得满地找牙的狠角色?”
顾天白略一偏头,琢磨片刻——那天他跟韩鯤鹏不过照面三合、错身两招,连衣角都没撕破,怎就传成了“满地找牙”?
殊不知看热闹的巷口街尾,专有那些嘴皮子比刀快、脑瓜子比鼓响的主儿。
话一出口,经三五张嘴来回嚼过,早变了味儿:什么“落花流水”反倒是最收敛的说法;
更有绘声绘色讲得活灵活现的,说顾天白与韩鯤鹏从酒楼二楼打到后巷井台,三百回合难分伯仲,最后抱拳一笑,相约秋后擂台再决高下——那架势,仿佛亲眼数过两人喘了几口气、眨了几回眼。
顾天白若听见这般,怕真要掏几文钱塞他手里,劝他去茶馆里掛牌说书去。
也有人嘀咕:“韩鯤鹏上楼到下楼,拢共不过半炷香工夫,连摔凳子的声音都没听见,哪来的三百回合?”
那嘴上生风的閒汉便一捋袖子:“高手交手,电光石火之间胜负已定!內里玄机,岂是你我凡胎肉眼看得穿的?”
话赶话,话叠话,两张嘴皮一碰,戏就开场了。
薄近侯自打正月初一就跟车队跑宋家拉货,这几日刚回历州,满心只想著替姨娘討个公道。
今儿头回听说——那位要教自己功夫的顾天白,竟还跟韩有鱼的哥哥韩鯤鹏有过一场硬碰硬。
第442章 有过一场硬碰硬
“要宣花斧。”顾天白补了一句。
娄圭眼神一顿,眸中疑云顿起。宣花斧?名头听著寻常,实则不是谁都能掂量的硬茬。
“打得出来?”顾天白再问。
娄圭目光扫过眼前这个比自己矮了一尺有余、面容清朗的青年,略一沉吟:“手边正好有块上好铁胚,申时来取,绝不误事。”他顿了顿,又问,“多重?”
“你能锻多重,我就用多重。”
满屋静了半拍。
顾天白先是一怔,隨即摇头苦笑;兄弟俩互看一眼,终於憋不住,噗嗤笑出声。
乾坤岂容狂徒立,敢摘星斗掷沧溟。
终究是少年心性。
薄近候却不管这些,张口就来一句,直把娄圭兄弟笑得前仰后合。
娄臬毫不客气,当场呛声:“我哥能打出百斤重的,你扛得动?!”
“你们锻得出来,我就扛得动。”薄近侯挺直腰杆,寸步不让,可那副绷紧脖颈、咬牙瞪眼的模样,在打铁兄弟眼里,倒像小孩儿赌气,倔得有点可爱。
“这兵刃费工是费工,却不算多难。今儿头一桩买卖,咱们图个吉利,让些利,整数一百两——定金先交一半。”
娄圭不像娄臬那般爱较劲,许是年长几岁,早明白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瞧他膀大腰圆、满脸煤灰,心却细如髮丝。
他怕顾天白二人拿自己寻开心,前前后后盘算得滴水不漏,连退路都悄悄留好了。
“一百两?你不如去府衙抢库银!”顾天白从小不把银钱当回事,这百两雪花银,够寻常三口之家吃穿嚼用六七年,於他不过帐本上一个墨点;
薄近侯却当场跳脚,仿佛对方不是做生意,而是抡著斧子拦路劫道。
“嫌贵?请便,门在那边。”娄臬嘴角一翘,神气活现,活像刚贏了场斗鸡——他和薄近侯年纪相仿,话赶话呛几句,倒像比谁嗓门更亮、谁脸皮更厚,输贏全写在脸上。
这话他確实说得硬气:歷下城里,別说找第二家能打利刃的铺子,就是百里之內,怕也寻不出第三处炉火通红的铁匠铺。
薄近侯一时语塞,手指抠著衣角,急得直挠后脑勺,嘴张了又合,愣是没挤出半个字来。
“只要东西扎实,价钱高低倒不打紧。”顾天白边说边摸出一张银票,手刚抬起来,却被薄近侯一把攥住手腕。
薄近侯心眼实在,肚子里没那么多弯弯绕。
在他看来,拜师得敬束脩,就像城里私塾里的学子,逢年过节拎著五花肉、提著老烧酒往先生家钻。
顾天白教他功夫,从没提过一个铜板,他早觉得这份情义重过千斤;如今再让他掏人家的钱买兵器?
他寧愿赤手空拳去劈柴,也不肯点头。
可对方这价码,真真是狮子甩尾——他给宋家跑腿送货三年,一年拢共才挣十几二十两;別说一百两,光那五十两定金,他翻遍所有口袋、借遍左邻右舍,也凑不出半文。
“怎么?”顾天白一怔,完全没料到他心里转著这许多念头。
“我……我自己来。”薄近侯声音发虚,话还没落地,耳根子就烫了起来。
顾天白目光一扫,心里顿时透亮:这傻小子正为钱发愁呢。他唇角微扬,语气轻快:“我先垫上,事成之后你再还我,乾净利落。”
话说得云淡风轻,薄近侯再憨也听明白了——这是替他兜著底,护著他那点可怜的面子,免得在外人面前露怯丟份。
有时一句话,暖得人骨头缝都酥;有时一句话,冷得人脊梁骨发僵。
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六月寒。
这哪是什么权术?不过是常年跟著姐姐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举手投足已沾上几分她的分寸与体谅。
娄臬接过银票,手竟微微发颤。
他这辈子头回摸著这么厚实的票子,反反覆覆对光瞧、指腹捻、对著窗缝吹气验——不是没见过世面,倒像是生怕它眨眼化作纸灰。
顾天白神色坦然:“钱一次结清,不必分什么定金尾款,麻烦。”
娄圭却突然抱拳躬身,声调也沉了几分:“敢问尊姓大名?”——这是进门以来,他头一回露出几分敬意。在他眼里,整个歷下城,能甩出百两银票还不眨一下眼的,掰著指头都数不满五人;
可眼前这张脸,他確確实实没见过。
顾天白这些年隨姐姐辗转奔走,反倒是在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歷下城里,被人频频问起名號。
若非这几日接连被问,他倒真想把那个让大周朝野听见就屏息噤声的姓氏,悄悄抹去。
“我住县南巷,先前在天然居落脚过些日子。若信不过这票子,尽可去天然居寻老板,他认得我,也知我落脚处。”顾天白答得乾脆,娄圭却猛地睁大双眼:“原来是你!”
“认得我?”顾天白微讶,旋即一笑——前几日那场风波,早传遍大街小巷,此刻听见这声惊呼,倒也不奇怪了。
娄臬手指直戳顾天白,舌头打结似的,“你……你不是那个……把杨家女婿揍得满地找牙的狠角色?”
顾天白略一偏头,琢磨片刻——那天他跟韩鯤鹏不过照面三合、错身两招,连衣角都没撕破,怎就传成了“满地找牙”?
殊不知看热闹的巷口街尾,专有那些嘴皮子比刀快、脑瓜子比鼓响的主儿。
话一出口,经三五张嘴来回嚼过,早变了味儿:什么“落花流水”反倒是最收敛的说法;
更有绘声绘色讲得活灵活现的,说顾天白与韩鯤鹏从酒楼二楼打到后巷井台,三百回合难分伯仲,最后抱拳一笑,相约秋后擂台再决高下——那架势,仿佛亲眼数过两人喘了几口气、眨了几回眼。
顾天白若听见这般,怕真要掏几文钱塞他手里,劝他去茶馆里掛牌说书去。
也有人嘀咕:“韩鯤鹏上楼到下楼,拢共不过半炷香工夫,连摔凳子的声音都没听见,哪来的三百回合?”
那嘴上生风的閒汉便一捋袖子:“高手交手,电光石火之间胜负已定!內里玄机,岂是你我凡胎肉眼看得穿的?”
话赶话,话叠话,两张嘴皮一碰,戏就开场了。
薄近侯自打正月初一就跟车队跑宋家拉货,这几日刚回历州,满心只想著替姨娘討个公道。
今儿头回听说——那位要教自己功夫的顾天白,竟还跟韩有鱼的哥哥韩鯤鹏有过一场硬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