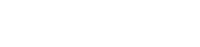综武:铁血霸主,从踏破北莽开始 作者:佚名
第432章 还装什么冰清玉洁
起初韩顶天也觉得丟了顏面,可怪就怪在,他嘴上骂几句,手却始终没伸过去管一管。
外头人都揣测,八成是把武当掌门那句“此子有异”当了真,至於內里究竟藏著什么盘算,怕是只有韩顶天自己心里亮堂。
偎红楼外,这会儿早已没了寻欢作乐的客人。
风韵犹存的白姨斜倚在门口茶台边,正跟旁边那个大茶壶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閒篇,眼角一扫,忽见远处晃来两个人,在楼门口站定,东张西望。
“哎哟——杨爷!今儿什么贵风吹您大驾光临?”徐娘半老的白姨眼波一转,立马堆起蜜糖似的笑,扭著腰迎上前,“要哪个姑娘,您差个人捎个话,我亲自领著送上门去,何苦让您跑这一趟?”
“去去去,少囉嗦!”杨富一路低眉顺眼,到了这儿才算鬆开筋骨,嗓门都亮了几分,“今儿陪我家二公子来挑挑鲜货。快著点,拣几个新来的,让我家公子过过眼。”
白姨闻言,顺势鬆开杨富胳膊,双手往胸前一环,顺势託了托那呼之欲出的丰润,眼尾一挑,千娇百媚地朝韩有鱼飘去。
这种销金窟是啥地方?三教九流全在这儿扎堆,三百六十行样样齐全——从门口招徠客人的掮客、端茶倒水的大茶壶,到台上唱曲儿的头牌、刚掛牌的清倌人,哪一个不是练就了一双毒辣眼睛?
更別说这位早退居幕后、轻易不露面的老鴇子。
“这位小哥面生得很吶,不知是哪家府上的贵人?”她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桃花眼弯成月牙,直勾勾落向韩有鱼。
看人先看相。白姨在这行里打滚几十年,一眼就瞧出端倪——这公子脸色泛青,眼皮浮肿,眼神浑浊,分明是纵情声色熬出来的虚火。
韩有鱼自小就被这些风流妇人哄著长大,也是个中老手。被白姨那双勾魂摄魄的眼一撩,他苍白的脸上竟浮起一层薄红,懒懒开口:“別问我是谁家的,只管把爷伺候舒坦了,怎么都好说。”
白姨一听这话,心下立时明了——是个熟客。眼梢笑意更深,抬手朝楼里招呼:“快出来!都给我精神点!”
谁知话音未落,韩有鱼忽然俯身,一把將她打横抱起,朗声笑道:“还喊什么女儿?你自个儿不就现成的?”任由她在他怀里扑腾挣扎,他脚步不停,大步跨进了楼门。
偎红楼四周围了不少人,听见白姨喊救命,却没一个敢上前拦的。这些人虽不认识这位公子,可杨富的脸,谁不认得?
连杨家管家都对他点头哈腰,谁还敢当这个出头鸟?
“姐,醒啦。”
窗前条案上,姐姐正伏著打盹,猛地一颤,茫然坐直。
“又做噩梦了?”清秀男子端著三年如一日的四菜一汤推门进来,把饭菜轻轻搁在桌上,快步上前扶她坐下,笑著问:“这回梦见啥了?狗追你,还是钱袋子飞了?”
听弟弟打趣,姐姐噗嗤一笑:“梦见我走了,某人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
弟弟摇头失笑。
她衝著窗外暖融融的日头伸了个懒腰,长长吐出一口闷气,鼻子动了动,闻见饭菜香,才恍然:“哟,该吃饭了?”
“这两日你哪天不是熬到后半夜,白天不困才稀奇。”他扶她往饭桌走,嘴上责备著,语气里却半点火气也无。
我哪料到这歷下城过年竟这般喧腾,年三十起就满街掛灯、彻夜开市,吃食琳琅、杂耍纷呈,人声鼎沸得连觉都睡不安稳,你快闻闻,快闻闻!
姐姐那玲瓏鼻尖又轻轻一颤,俏皮地耸了耸,眉眼弯弯,“扑面而来的这是什么香?是年气——是糟滷的醇厚、桃花面的清甜、烤驼峰的焦香,更是寻常人家碗里有肉、灶上有火的踏实滋味。”
弟弟哼了一声,扭过头去,懒得接话,分明拿这个“不务正业”的姐姐毫无办法。
姐姐却忽地一怔,眼神凝住,声音压低:“天白,对面楼上……有人在喊救命。”
被唤作天白的弟弟笑著摇头:“你又不是不晓得对面是哪儿,三教九流扎堆的地界,偏爱折腾些出格名堂的人多了去了。”他一边把碗筷往姐姐手里塞,一边隨口道,“兴许今儿又闯进个疯癲货色也未可知。”
姐姐却断然摇头,柳眉微锁:“绝不是玩笑。”
天白失笑出声。
她虽是幼时失明,可这些年耳聪手敏、鼻观入微,反比常人更锐利三分;有时连他这个日日淬炼筋骨、耳力目力皆已超凡的弟弟听不见的细响,她也能辨得分明。
“少操閒心,再囉嗦,我真拿棉絮堵你耳朵。”天白故意板起脸打趣。
姐姐仍蹙著眉,指尖捏著筷子,在碗沿上无意识轻点,饭粒拨来拨去,迟迟不动口。
“哐啷——!”
一声脆响如惊雷劈开空气,紧跟著是一声悽厉惨叫,震得姐姐手一抖,筷子脱指落地,她霍然起身,快步挪到窗边,屏息凝神,侧耳细听对面动静。
纵使眼前漆黑一片,可那楼上传来的每一丝喘息、每一声闷响,都像刻在她耳膜上般清晰。
“当老鴇的骨头都贱透了,还装什么冰清玉洁!”
客栈斜对面,歷下城最奢靡的销金窟——偎红楼二层,一扇豁口迸裂的窗框旁,传来一句阴狠毒辣的叱喝。
“是偎红楼的白姨!”
楼上楼下、街左街右,霎时炸开一片惊呼。
“还有气吗?”姐姐侧过脸,朝刚踱到身边的天白轻声问。
“没救了。”天白语气沉了几分,伸手扶住她手臂,引她缓缓回座,声音里裹著一丝不忍,“从那么高摔下来,神仙来了也续不上命。也不知谁火气这么大,活生生把人推下去。”
待她坐定,他又添一句:“吃饭就安安静静吃饭,掺和这些做什么?”
“太惨了。”姐姐眉心拧得更紧,“我早说那声呼救不对劲,如今……人没了。”
天白咧嘴一笑:“不是早劝你莫伸手?照你这副菩萨心肠,偎红楼上下几十个姑娘,我怕是要连夜扛梯子挨个背出来。”
姐姐没好气,抄起筷子朝他额角轻轻一敲:“总好过眼睁睁看著一条命断在眼皮底下。”
天白撇嘴,心里清楚得很——她一旦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拽不回来。
饭是吃不下了,她呆坐著,筷子在碗里漫无目的地扒拉著几粒冷饭,心思早已飘远。
楼下忽地乱了起来,呵斥声、踢踏声、杂沓脚步声由远及近,噔噔噔直撞上楼。
“咣嘰!”
那扇薄木门哪里经得起这一脚猛踹,应声碎裂,木屑飞溅。
一个穿亚麻青衫、腰缠草绳、別著把象牙白摺扇的公子哥儿晃晃悠悠跨进门来,衣裳不伦不类,脸色泛著酒色淘空后的青白,嘴角却掛著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笑意。
“我就篤定这小娘子住这儿。”他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黏在屋中唯一的女子身上,眼神灼灼,语调懒散又轻佻,“小爷的眼,错不了。”
正是韩有鱼。
方才在偎红楼里,他真没想到那风韵犹存的妇人竟能如此硬气——任他威逼利诱、软磨硬泡,她只咬牙绷著不肯就范。
这几日年节纵情酒色,身子早虚得发飘,力气竟也压不住一个中年妇人,反倒让他疑心:这熬成鴇母的女人,莫非是在他面前演戏?
推搡间,他恼羞成怒一发力,竟失手將人搡出窗外——於是,便有了方才那一声坠落、一声哀嚎。
短暂的惊骇过后,韩有鱼反倒神色如常——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一条人命,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银票能填平的沟壑。
可就在转身欲走、兴致全无之际,
第432章 还装什么冰清玉洁
起初韩顶天也觉得丟了顏面,可怪就怪在,他嘴上骂几句,手却始终没伸过去管一管。
外头人都揣测,八成是把武当掌门那句“此子有异”当了真,至於內里究竟藏著什么盘算,怕是只有韩顶天自己心里亮堂。
偎红楼外,这会儿早已没了寻欢作乐的客人。
风韵犹存的白姨斜倚在门口茶台边,正跟旁边那个大茶壶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閒篇,眼角一扫,忽见远处晃来两个人,在楼门口站定,东张西望。
“哎哟——杨爷!今儿什么贵风吹您大驾光临?”徐娘半老的白姨眼波一转,立马堆起蜜糖似的笑,扭著腰迎上前,“要哪个姑娘,您差个人捎个话,我亲自领著送上门去,何苦让您跑这一趟?”
“去去去,少囉嗦!”杨富一路低眉顺眼,到了这儿才算鬆开筋骨,嗓门都亮了几分,“今儿陪我家二公子来挑挑鲜货。快著点,拣几个新来的,让我家公子过过眼。”
白姨闻言,顺势鬆开杨富胳膊,双手往胸前一环,顺势託了托那呼之欲出的丰润,眼尾一挑,千娇百媚地朝韩有鱼飘去。
这种销金窟是啥地方?三教九流全在这儿扎堆,三百六十行样样齐全——从门口招徠客人的掮客、端茶倒水的大茶壶,到台上唱曲儿的头牌、刚掛牌的清倌人,哪一个不是练就了一双毒辣眼睛?
更別说这位早退居幕后、轻易不露面的老鴇子。
“这位小哥面生得很吶,不知是哪家府上的贵人?”她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桃花眼弯成月牙,直勾勾落向韩有鱼。
看人先看相。白姨在这行里打滚几十年,一眼就瞧出端倪——这公子脸色泛青,眼皮浮肿,眼神浑浊,分明是纵情声色熬出来的虚火。
韩有鱼自小就被这些风流妇人哄著长大,也是个中老手。被白姨那双勾魂摄魄的眼一撩,他苍白的脸上竟浮起一层薄红,懒懒开口:“別问我是谁家的,只管把爷伺候舒坦了,怎么都好说。”
白姨一听这话,心下立时明了——是个熟客。眼梢笑意更深,抬手朝楼里招呼:“快出来!都给我精神点!”
谁知话音未落,韩有鱼忽然俯身,一把將她打横抱起,朗声笑道:“还喊什么女儿?你自个儿不就现成的?”任由她在他怀里扑腾挣扎,他脚步不停,大步跨进了楼门。
偎红楼四周围了不少人,听见白姨喊救命,却没一个敢上前拦的。这些人虽不认识这位公子,可杨富的脸,谁不认得?
连杨家管家都对他点头哈腰,谁还敢当这个出头鸟?
“姐,醒啦。”
窗前条案上,姐姐正伏著打盹,猛地一颤,茫然坐直。
“又做噩梦了?”清秀男子端著三年如一日的四菜一汤推门进来,把饭菜轻轻搁在桌上,快步上前扶她坐下,笑著问:“这回梦见啥了?狗追你,还是钱袋子飞了?”
听弟弟打趣,姐姐噗嗤一笑:“梦见我走了,某人哭得鼻涕眼泪糊一脸。”
弟弟摇头失笑。
她衝著窗外暖融融的日头伸了个懒腰,长长吐出一口闷气,鼻子动了动,闻见饭菜香,才恍然:“哟,该吃饭了?”
“这两日你哪天不是熬到后半夜,白天不困才稀奇。”他扶她往饭桌走,嘴上责备著,语气里却半点火气也无。
我哪料到这歷下城过年竟这般喧腾,年三十起就满街掛灯、彻夜开市,吃食琳琅、杂耍纷呈,人声鼎沸得连觉都睡不安稳,你快闻闻,快闻闻!
姐姐那玲瓏鼻尖又轻轻一颤,俏皮地耸了耸,眉眼弯弯,“扑面而来的这是什么香?是年气——是糟滷的醇厚、桃花面的清甜、烤驼峰的焦香,更是寻常人家碗里有肉、灶上有火的踏实滋味。”
弟弟哼了一声,扭过头去,懒得接话,分明拿这个“不务正业”的姐姐毫无办法。
姐姐却忽地一怔,眼神凝住,声音压低:“天白,对面楼上……有人在喊救命。”
被唤作天白的弟弟笑著摇头:“你又不是不晓得对面是哪儿,三教九流扎堆的地界,偏爱折腾些出格名堂的人多了去了。”他一边把碗筷往姐姐手里塞,一边隨口道,“兴许今儿又闯进个疯癲货色也未可知。”
姐姐却断然摇头,柳眉微锁:“绝不是玩笑。”
天白失笑出声。
她虽是幼时失明,可这些年耳聪手敏、鼻观入微,反比常人更锐利三分;有时连他这个日日淬炼筋骨、耳力目力皆已超凡的弟弟听不见的细响,她也能辨得分明。
“少操閒心,再囉嗦,我真拿棉絮堵你耳朵。”天白故意板起脸打趣。
姐姐仍蹙著眉,指尖捏著筷子,在碗沿上无意识轻点,饭粒拨来拨去,迟迟不动口。
“哐啷——!”
一声脆响如惊雷劈开空气,紧跟著是一声悽厉惨叫,震得姐姐手一抖,筷子脱指落地,她霍然起身,快步挪到窗边,屏息凝神,侧耳细听对面动静。
纵使眼前漆黑一片,可那楼上传来的每一丝喘息、每一声闷响,都像刻在她耳膜上般清晰。
“当老鴇的骨头都贱透了,还装什么冰清玉洁!”
客栈斜对面,歷下城最奢靡的销金窟——偎红楼二层,一扇豁口迸裂的窗框旁,传来一句阴狠毒辣的叱喝。
“是偎红楼的白姨!”
楼上楼下、街左街右,霎时炸开一片惊呼。
“还有气吗?”姐姐侧过脸,朝刚踱到身边的天白轻声问。
“没救了。”天白语气沉了几分,伸手扶住她手臂,引她缓缓回座,声音里裹著一丝不忍,“从那么高摔下来,神仙来了也续不上命。也不知谁火气这么大,活生生把人推下去。”
待她坐定,他又添一句:“吃饭就安安静静吃饭,掺和这些做什么?”
“太惨了。”姐姐眉心拧得更紧,“我早说那声呼救不对劲,如今……人没了。”
天白咧嘴一笑:“不是早劝你莫伸手?照你这副菩萨心肠,偎红楼上下几十个姑娘,我怕是要连夜扛梯子挨个背出来。”
姐姐没好气,抄起筷子朝他额角轻轻一敲:“总好过眼睁睁看著一条命断在眼皮底下。”
天白撇嘴,心里清楚得很——她一旦认准的事,八匹马都拽不回来。
饭是吃不下了,她呆坐著,筷子在碗里漫无目的地扒拉著几粒冷饭,心思早已飘远。
楼下忽地乱了起来,呵斥声、踢踏声、杂沓脚步声由远及近,噔噔噔直撞上楼。
“咣嘰!”
那扇薄木门哪里经得起这一脚猛踹,应声碎裂,木屑飞溅。
一个穿亚麻青衫、腰缠草绳、別著把象牙白摺扇的公子哥儿晃晃悠悠跨进门来,衣裳不伦不类,脸色泛著酒色淘空后的青白,嘴角却掛著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笑意。
“我就篤定这小娘子住这儿。”他双臂抱在胸前,目光黏在屋中唯一的女子身上,眼神灼灼,语调懒散又轻佻,“小爷的眼,错不了。”
正是韩有鱼。
方才在偎红楼里,他真没想到那风韵犹存的妇人竟能如此硬气——任他威逼利诱、软磨硬泡,她只咬牙绷著不肯就范。
这几日年节纵情酒色,身子早虚得发飘,力气竟也压不住一个中年妇人,反倒让他疑心:这熬成鴇母的女人,莫非是在他面前演戏?
推搡间,他恼羞成怒一发力,竟失手將人搡出窗外——於是,便有了方才那一声坠落、一声哀嚎。
短暂的惊骇过后,韩有鱼反倒神色如常——他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一条人命,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银票能填平的沟壑。
可就在转身欲走、兴致全无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