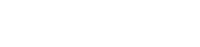听到周娜娜说出这句话,徐波琢磨了一下,跳进时光隧道里,寻找记忆里的那些女人。
从青梅竹马已经死去的小花,再到人间蒸发的於晓霞,再到纯白如纸的翠翠,徐波点头认同了周娜娜的话,一个女人一个味。
周娜娜见徐波点头,便意味深长的问了一句:“徐波,你知道爱情是啥样的么?”
这个问题再次让徐波沉思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周娜娜察觉到徐波脸上的疑惑,笑了笑说:“徐波,我告诉你,真正的爱情不是野鸳鸯,野鸳鸯註定被人喊打,真正的爱情是光明正大,不是偷偷摸摸。”
徐波瞪大眼睛说:“秋姐,你是说梁山伯和祝英台?”
周娜娜无语的笑了,拍了一下徐波的脑袋说:“爱情是有美好结局的,而不是一同赴死殉情,懂么?”
徐波憨笑一下,“我明白了,就像我爹娘那样。”
周娜娜咀嚼了一下徐波的这句话,点点头说:“也不算,你爹妈最多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找对了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巧合。”
她的话说完,徐波嘿嘿笑了笑,眼睛盯著周娜娜漂亮的脸蛋,说:“秋姐,那你说,是不是一个男人一个味?”
周娜娜哈哈笑了几声,抬手捏住徐波的鼻子,说:“你这傻小子,还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財富上的皇帝,肉体上的乞丐,明白么?”
“明白。”徐波说。
周娜娜哼笑一声:“明白个屁,男人都是一个味,臭味。”
隨后周娜娜又说:“去看看你的翠翠去吧。”
徐波哦了一声,站起身走了出去。
下楼来到马煜雯的病房,这间普通病房有四个床位,马煜雯躺在靠窗的那个病床上。
翠翠坐在床边凳子上,双手托腮看著缠著纱布马煜雯的脸发呆。
徐波走过去,拍了拍翠翠肩膀说:“翠,想啥呢?”
翠翠没看到徐波走进来,被嚇了一跳,扭头看著徐波,咧嘴一笑说:“没想啥,我就是想看看小雯姐的脸啥样了。”
隨后翠翠又说:“能拆开她纱布看看吗?”
徐波摇头:“不行,她脸受伤了,拆开纱布会很疼。”
“比舅妈惩罚我的时候还要疼吗?”翠翠问。
徐波揽住翠翠的肩膀,说:“翠,想回家么?”
“哪个家?”翠翠问。
“我的家。”徐波说。
翠翠脸上的表情掠过四季,停在了春天,开出一朵花,嘻嘻笑著说:“我想回家,想阿姨,想大鹅,想叔叔。”
“等元旦放假,我带你回家。”徐波说。
“咱厂那么忙,元旦会放假吗?”翠翠诧异的问。
“你舅妈说会。”徐波回道。
…………
光阴穿梭,两天后,周娜娜出了院,马煜雯继续住院,翠翠被替换出来,换了个大婶陪床。
徐波回到厂,车间依旧尘土飞扬,机器依旧轰隆隆的忙碌著。
车间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叫蒋艷梅,嘴上有痣,是个话癆,她是別的车间调过来的车间统计,替代了翠翠的职位。
徐波从马盈嘴里知道了一件事,城东南那家失火的酒厂厂长,被人打断了两条腿,在医院里躺著。
四天后,周娜娜开著一辆新换的车,拉著徐波和翠翠去参加她朋友的婚礼,新车是奥迪。
酒店是星级,结婚典礼在顶层一个大厅里,大厅布置的五彩繽纷,喜气洋洋,大厅的音响里播放著那首歌曲《好日子》。
周娜娜和徐波还有翠翠在酒桌旁挨在一起,翠翠將一根螃蟹腿塞进嘴里,吸的津津有味。
台上的新郎是一个方脸的中年大叔,西装领带,鼻樑上架著眼镜,看上去挺有文化,又像个扶贫的老干部。
新娘盘著头穿著白婚纱,身材没腰,很富態。
结婚典礼进行了一半,新娘笑眯眯跑到酒桌旁,拉著周娜娜上了台。
上台后,新娘拿著话筒搂著周娜娜,激动的对著台下宾客说:“她是我好朋友好闺蜜,才三十出头,是企业家,还没对象哦。”
周娜娜脸上表情有点尷尬,新娘对周娜娜说:“娜娜,今天是我大喜日子,你得给我整个节目,不然我诅咒你一辈子单身。”
周娜娜被这个诅咒嚇了一跳,想了想,指著台下一个酒桌说:“我和我朋友唱首歌吧。”
新娘立即鼓掌,问:“是谁啊?”
周娜娜走下台,把徐波拽了上来,俩人合唱了一首《选择》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角到天涯,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
周娜娜唱的很投入,徐波唱的额头冒出了汗。
翠翠坐在酒桌旁,手握著筷子,眼睛盯著台上唱歌的舅妈和徐波,忽然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是委屈么?翠翠自己都不知道。
一场欢天喜地的婚礼结束了,客人兜里揣著糖,各回各家。
周娜娜开车拉著二人回家,徐波和翠翠坐在车后座,翠翠低著头嘟著嘴巴,徐波发觉翠翠有些不高兴,便问:“咋了翠?”
翠翠嘴巴一瘪,哭了出来,脑袋埋在徐波肩膀,说:“徐大哥,你別丟了我啊,別丟了我…”
徐波搂住她,“翠別哭,我咋会丟了你啊。”
双手握著方向盘的周娜娜眼睛望著前方的路,咬著嘴唇,一言不发。
此时翠翠弯著腰趴在周娜娜座椅的椅背,说:“舅妈,我的户口本啥时候找到啊?”
周娜娜哦了一声,扭头说:“小翠別急,元旦放假我就去找。”
“那我跟你一块去找。”翠翠说。
“我去南方,很远,你和徐波待在家里等著。”周娜娜说。
把徐波和翠翠送回出租屋,周娜娜开车返回了厂。
回厂进入办公室,办公室里一堆人,烟雾繚绕。
哥哥周毅雄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靠墙的沙发上,坐著三个人。
周娜娜扫了眼那三个人,认出其中的两个人,是局里的。
周毅雄见妹妹走进来,便说:“小娜,上边下达任务了,明年正月底,就要把工厂的拆迁工作完成。”
听到哥哥的话,周娜娜愣住了,隨后说:“哥,这不可能啊,新厂还没完工,正月里又不能开工,咋搬迁厂子?”
周毅雄嘆了口气说:“办法总是人想的嘛,总有办法的。”
周娜娜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头猪,被赶进了死胡同,猪爬不上墙,也拱不倒墙。
周娜娜看向沙发上坐著的三人,说:“能不能把时间往后拖一拖,再延后一个月。”
坐在沙发中间的一个中年人呵呵笑了笑,摸了摸自己仙人球一样的髮型,说:“周老板,我们也很无奈啊,政策之下,我们都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周娜娜抿著嘴,点了点头,苦笑一声。
这三人走后,周娜娜坐在哥哥对面,说:“送礼不行么?”
周毅雄摇摇头,“不行,小礼没用,大礼咱也拿不出来,你別忘了,咱还有一千多万的贷款。”
周娜娜深吸一口气,“给我根烟。”
普通人的命运像一湾湖水,丟下一颗石子,波纹都盪不到岸边,就恢復平静。
……
1999年的年底,翻过一页,到了元旦。
2000年是千禧年,工厂元旦放了三天假,周娜娜只身去了南方。
马煜雯出了院,她伤好的差不多了,脸也没毁容,她在跳楼的时候,双手捂住了脸,脸是面,面毁了,这一辈子基本就毁了,马煜雯保住了这一辈子。
元旦放假,马煜雯邀请翠翠去她老家玩,翠翠原本打算跟著徐波去他老家,但还是问了句:“小雯姐,你老家好玩吗?”
马煜雯浅笑,酒窝浮现在嘴角,抓著翠翠的手说:“好玩著呢,你不是喜欢爬山吗?我老家有好多山。”
“嘻嘻,那我跟你去,但徐大哥我要带著。”翠翠喜滋滋说。
“当然啊,咱一块去。”马煜雯说。
从青梅竹马已经死去的小花,再到人间蒸发的於晓霞,再到纯白如纸的翠翠,徐波点头认同了周娜娜的话,一个女人一个味。
周娜娜见徐波点头,便意味深长的问了一句:“徐波,你知道爱情是啥样的么?”
这个问题再次让徐波沉思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周娜娜察觉到徐波脸上的疑惑,笑了笑说:“徐波,我告诉你,真正的爱情不是野鸳鸯,野鸳鸯註定被人喊打,真正的爱情是光明正大,不是偷偷摸摸。”
徐波瞪大眼睛说:“秋姐,你是说梁山伯和祝英台?”
周娜娜无语的笑了,拍了一下徐波的脑袋说:“爱情是有美好结局的,而不是一同赴死殉情,懂么?”
徐波憨笑一下,“我明白了,就像我爹娘那样。”
周娜娜咀嚼了一下徐波的这句话,点点头说:“也不算,你爹妈最多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找对了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巧合。”
她的话说完,徐波嘿嘿笑了笑,眼睛盯著周娜娜漂亮的脸蛋,说:“秋姐,那你说,是不是一个男人一个味?”
周娜娜哈哈笑了几声,抬手捏住徐波的鼻子,说:“你这傻小子,还想套我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財富上的皇帝,肉体上的乞丐,明白么?”
“明白。”徐波说。
周娜娜哼笑一声:“明白个屁,男人都是一个味,臭味。”
隨后周娜娜又说:“去看看你的翠翠去吧。”
徐波哦了一声,站起身走了出去。
下楼来到马煜雯的病房,这间普通病房有四个床位,马煜雯躺在靠窗的那个病床上。
翠翠坐在床边凳子上,双手托腮看著缠著纱布马煜雯的脸发呆。
徐波走过去,拍了拍翠翠肩膀说:“翠,想啥呢?”
翠翠没看到徐波走进来,被嚇了一跳,扭头看著徐波,咧嘴一笑说:“没想啥,我就是想看看小雯姐的脸啥样了。”
隨后翠翠又说:“能拆开她纱布看看吗?”
徐波摇头:“不行,她脸受伤了,拆开纱布会很疼。”
“比舅妈惩罚我的时候还要疼吗?”翠翠问。
徐波揽住翠翠的肩膀,说:“翠,想回家么?”
“哪个家?”翠翠问。
“我的家。”徐波说。
翠翠脸上的表情掠过四季,停在了春天,开出一朵花,嘻嘻笑著说:“我想回家,想阿姨,想大鹅,想叔叔。”
“等元旦放假,我带你回家。”徐波说。
“咱厂那么忙,元旦会放假吗?”翠翠诧异的问。
“你舅妈说会。”徐波回道。
…………
光阴穿梭,两天后,周娜娜出了院,马煜雯继续住院,翠翠被替换出来,换了个大婶陪床。
徐波回到厂,车间依旧尘土飞扬,机器依旧轰隆隆的忙碌著。
车间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叫蒋艷梅,嘴上有痣,是个话癆,她是別的车间调过来的车间统计,替代了翠翠的职位。
徐波从马盈嘴里知道了一件事,城东南那家失火的酒厂厂长,被人打断了两条腿,在医院里躺著。
四天后,周娜娜开著一辆新换的车,拉著徐波和翠翠去参加她朋友的婚礼,新车是奥迪。
酒店是星级,结婚典礼在顶层一个大厅里,大厅布置的五彩繽纷,喜气洋洋,大厅的音响里播放著那首歌曲《好日子》。
周娜娜和徐波还有翠翠在酒桌旁挨在一起,翠翠將一根螃蟹腿塞进嘴里,吸的津津有味。
台上的新郎是一个方脸的中年大叔,西装领带,鼻樑上架著眼镜,看上去挺有文化,又像个扶贫的老干部。
新娘盘著头穿著白婚纱,身材没腰,很富態。
结婚典礼进行了一半,新娘笑眯眯跑到酒桌旁,拉著周娜娜上了台。
上台后,新娘拿著话筒搂著周娜娜,激动的对著台下宾客说:“她是我好朋友好闺蜜,才三十出头,是企业家,还没对象哦。”
周娜娜脸上表情有点尷尬,新娘对周娜娜说:“娜娜,今天是我大喜日子,你得给我整个节目,不然我诅咒你一辈子单身。”
周娜娜被这个诅咒嚇了一跳,想了想,指著台下一个酒桌说:“我和我朋友唱首歌吧。”
新娘立即鼓掌,问:“是谁啊?”
周娜娜走下台,把徐波拽了上来,俩人合唱了一首《选择》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角到天涯,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
周娜娜唱的很投入,徐波唱的额头冒出了汗。
翠翠坐在酒桌旁,手握著筷子,眼睛盯著台上唱歌的舅妈和徐波,忽然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是委屈么?翠翠自己都不知道。
一场欢天喜地的婚礼结束了,客人兜里揣著糖,各回各家。
周娜娜开车拉著二人回家,徐波和翠翠坐在车后座,翠翠低著头嘟著嘴巴,徐波发觉翠翠有些不高兴,便问:“咋了翠?”
翠翠嘴巴一瘪,哭了出来,脑袋埋在徐波肩膀,说:“徐大哥,你別丟了我啊,別丟了我…”
徐波搂住她,“翠別哭,我咋会丟了你啊。”
双手握著方向盘的周娜娜眼睛望著前方的路,咬著嘴唇,一言不发。
此时翠翠弯著腰趴在周娜娜座椅的椅背,说:“舅妈,我的户口本啥时候找到啊?”
周娜娜哦了一声,扭头说:“小翠別急,元旦放假我就去找。”
“那我跟你一块去找。”翠翠说。
“我去南方,很远,你和徐波待在家里等著。”周娜娜说。
把徐波和翠翠送回出租屋,周娜娜开车返回了厂。
回厂进入办公室,办公室里一堆人,烟雾繚绕。
哥哥周毅雄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靠墙的沙发上,坐著三个人。
周娜娜扫了眼那三个人,认出其中的两个人,是局里的。
周毅雄见妹妹走进来,便说:“小娜,上边下达任务了,明年正月底,就要把工厂的拆迁工作完成。”
听到哥哥的话,周娜娜愣住了,隨后说:“哥,这不可能啊,新厂还没完工,正月里又不能开工,咋搬迁厂子?”
周毅雄嘆了口气说:“办法总是人想的嘛,总有办法的。”
周娜娜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头猪,被赶进了死胡同,猪爬不上墙,也拱不倒墙。
周娜娜看向沙发上坐著的三人,说:“能不能把时间往后拖一拖,再延后一个月。”
坐在沙发中间的一个中年人呵呵笑了笑,摸了摸自己仙人球一样的髮型,说:“周老板,我们也很无奈啊,政策之下,我们都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周娜娜抿著嘴,点了点头,苦笑一声。
这三人走后,周娜娜坐在哥哥对面,说:“送礼不行么?”
周毅雄摇摇头,“不行,小礼没用,大礼咱也拿不出来,你別忘了,咱还有一千多万的贷款。”
周娜娜深吸一口气,“给我根烟。”
普通人的命运像一湾湖水,丟下一颗石子,波纹都盪不到岸边,就恢復平静。
……
1999年的年底,翻过一页,到了元旦。
2000年是千禧年,工厂元旦放了三天假,周娜娜只身去了南方。
马煜雯出了院,她伤好的差不多了,脸也没毁容,她在跳楼的时候,双手捂住了脸,脸是面,面毁了,这一辈子基本就毁了,马煜雯保住了这一辈子。
元旦放假,马煜雯邀请翠翠去她老家玩,翠翠原本打算跟著徐波去他老家,但还是问了句:“小雯姐,你老家好玩吗?”
马煜雯浅笑,酒窝浮现在嘴角,抓著翠翠的手说:“好玩著呢,你不是喜欢爬山吗?我老家有好多山。”
“嘻嘻,那我跟你去,但徐大哥我要带著。”翠翠喜滋滋说。
“当然啊,咱一块去。”马煜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