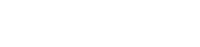黄沙被马蹄碾成齏粉,项少龙望著公子嘉身后“勤王”大旗,手下意识往怀中摸去,指尖触著一冰冷器物,心中大定。
“公子嘉远在代郡,”他按住剑柄的左手忽然改向,“怎会突然出现在此?”话音未落,身后魏將突然暴起,长剑直取他后心。
项少龙旋身避开的同时,火銃滑入掌心,枪口抵住对方咽喉——这是秦地秘坊打造的连珠火銃,內置七枚铅弹,半年前他用二十车金银財宝从墨家叛徒手中换得,据说是他们巨子所发明,这世界有点乱吶!
“砰!砰!”
两声若惊雷,魏將倒地,公子嘉捂著脖子,低头看了眼,血箭四射,发出嘶嘶漏气声
“你…你怎敢杀我?!”
公子嘉震惊,瞳孔逐渐涣散,不甘与遗憾隨著生机而逝去……
“私吞藏甲?”他扣动火銃扳机,又是一声枪响。
“且看这藏甲究竟属於谁!”项少龙挥刀劈开木箱,內里竟滚出刻著“嘉”字的青铜戈。
一幕僚脸色骤变,这些兵器是公子嘉半年前在代郡私铸,为的就是效仿李牧蓄养私兵。郭开忽然福至心灵,颤声喊道:“公子嘉私造兵器,意图谋反!”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项少龙调转枪口,连珠火銃的轰鸣震得树叶簌簌落下。勤王军前排的北军旧部轰然跪地,他们曾在李牧帐下听闻“秦军有弩车连射”,却从未想过有人能將如此利器藏在掌心。
……
……
咸阳宫的司天台传来更鼓声,贏乐望著铜镜里自己刻意点染的黑眼圈,捏皱了案头的密报。项少龙在桃林塞全歼公子嘉部的消息用硃砂圈了又圈,旁边批註著“火銃连杀三將”——这是韩夫人密信里从未提过的杀招。
“陛下,王翦求见。”宦官的通报声打断思绪,老將入殿时未著甲冑,只在腰间別了柄寻常青铜剑。
“项少龙已过函谷,”王翦將一卷舆图铺在地上,“其前锋距咸阳不过百里。”舆图上用红笔圈出三处隘口,贏乐的目光落在“灞上”標记上,那里曾是王翦二十年前驻军之处,如今却成了项少龙的必经之路。
“將军觉得该如何应对?”他故意將“將军”二字咬得极重,王翦的手指在“驪山”字样上顿住。老將忽然从怀中掏出个蜡丸,里面是项少龙兵营的布防图——標註者的笔跡,竟与韩夫人的密信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项少龙的中军帐內瀰漫著药石气息。他拆开雅夫人最新密信,“贏乐知蛊”四字被涂改成“王翦有图”,末尾画著司天台的星象图——那是咸阳宫密道的另一个入口。
“將军,”副將压低声音,“那墨家工匠说,这种连珠火銃最多再射三次,簧片就会断裂。”项少龙摩挲著枪管上的纹路,陷入沉思。
他转头望向帐外,公子嘉的残部正在整编,那些北军旧部看著他腰间的箭囊,眼神已从敌意转为敬畏。
………
………
咸阳城外三十里,渭水被初阳染成熔铁般的赤红色。项少龙立於战车之上,黑色披风在燥热的晨风中猎猎作响。他身后是三国联军——赵军飞燕旗、楚军赤凤幡、魏国苍狼徽在沙尘中连成一片血色海洋。
“报!秦军阵中异动!“斥候嗓音嘶哑,“那些铜怪物...在列阵!“
项少龙眯眼远眺。地平线上,数十尊三米高的青铜机关兽正缓缓展开躯体,关节处喷出蒸汽白烟。最前排的机关兽突然集体仰头,喉间齿轮转动发出刺耳的金属嘶鸣。
“装神弄鬼。“项少龙冷笑,挥手间三百架投石机同时扬起,“让他们见识下真正的'战爭'!“
三千枚陶罐火雷被投石机拋向秦军左翼。这些看似粗陋的土罐在半空突然裂开,洒下漫天火油,紧接著火箭齐发——
“轰!“
渭水北岸瞬间化作火海,三十名秦军来不及分散就被气浪掀飞。但火焰中突然衝出五头机关兽,它们覆满铜鳞的背部“咔嗒“翻起钢板,竟將燃烧的油脂尽数抖落!
“换毒气弹!“项少龙怒吼。
第二轮投射的陶罐在半空炸出绿色毒烟,最前排的机关兽突然踉蹌——毒雾腐蚀了齿轮间的松脂润滑剂!
………
战鼓突然转为急骤的密点,如丧钟般捶打每人心臟。秦军黑底狼首战旗下,方阵如活物般裂开,三百名轻甲兵士上场,手持燧发枪,踩著同一节拍推进,鹿皮护腕蹭过枪管的沙沙声里,第一排枪口已喷出白烟。铅弹撕裂两名楚军盾牌手的胸甲,血在青铜圆盾上绽开时,后排机关兽的巨掌碾碎满地断箭,战鼓每响一声,便逼近三步。
那尊“伐天巨兽“伏低的脊背最先撞破硝烟,青铜鳞片在血光中泛起幽蓝,四爪刨起的碎石打在联军盾牌上叮噹作响。楚军百夫长刚要喝令放箭,却见那庞然大物突然人立而起,前肢的青铜护套轰然展开,原本下垂的伐木斧“咔嗒“弹出七道锯齿,在夕阳下连成三米长的弧形光刃,锯齿间还掛著未乾的褐色黏液——不知是多少人的血与脑浆凝结而成。
“放——“
喝令戛然而止。锯齿刃横扫的瞬间,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排头十二名弓手连人带弓被齐齐削断,上半身飞坠时,腰腹断口的血柱喷得比盾牌还高。更骇人的是锯刃触血的剎那,锯齿突然向內翻转,整把刃口竟化作高速旋转的钻头,將落地的尸体绞成肉泥,混著碎骨的血雾被甩向后方,前排盾牌手的青铜面甲上顿时糊满温热的黏浆,透过呼吸孔钻进鼻腔的,是混杂著铁锈味的肝腥味。
机关兽的喉管里传出齿轮摩擦的尖啸,竟与秦军战鼓的节奏严丝合缝。它前爪踏碎一名试图爬走的伤兵,钻头般的刃口突然刺入地面,带起的碎石如霰弹般扫过第二排楚军,几名士兵的眼球被石片直接撞出眼眶。更令人胆寒的是它背部的青铜舱盖缓缓打开,两名秦军锐士戴著兽首面具,站在液压升降台上举著喷火器,粘稠的火油顺著兽嘴状喷口滴落,在焦土上滋滋冒烟。
“后撤!后撤!“楚军指挥旗开始疯狂摇晃,但伐天巨兽的铁尾已如青铜柱般扫来,扫中一名旗手的瞬间,尾端的三稜锥突然弹出,將人钉在身后的拒马桩上,旗杆上的“楚“字大旗被血浸透,在夜风中沉甸甸地垂下,宛如一块正在凝固的血布。燧发枪手的第二轮齐射恰在此时轰鸣,铅弹穿透盾牌的闷响与机关兽的金属嘶吼交织,渭水北岸的暮色,已被染成浓得化不开的黑红。
……
大帐內,项少龙气欲吐血,为什么机关兽都出现了?!早知这么乱,攻什么咸阳吶,立即逃往海外猥琐发育才是王道。
抚过腰间鹿皮袋里的青铜虎符,此刻正被掌心的冷汗浸得发烫。
“来人!派八百死士!备…”
副將陈武率八百死士伏在土坡,后背的陶瓮隨著呼吸轻晃,鱼油混合硫磺的刺鼻气味钻进甲缝,与每个人喉间的铁腥味酿成苦胆般的滋味。他余光扫过身旁的老兵,那人左脸的刀疤从眼角划到下頜,正用断指的手蘸著血,在陶瓮上歪歪扭扭画著家乡的麦穗。
“公子嘉远在代郡,”他按住剑柄的左手忽然改向,“怎会突然出现在此?”话音未落,身后魏將突然暴起,长剑直取他后心。
项少龙旋身避开的同时,火銃滑入掌心,枪口抵住对方咽喉——这是秦地秘坊打造的连珠火銃,內置七枚铅弹,半年前他用二十车金银財宝从墨家叛徒手中换得,据说是他们巨子所发明,这世界有点乱吶!
“砰!砰!”
两声若惊雷,魏將倒地,公子嘉捂著脖子,低头看了眼,血箭四射,发出嘶嘶漏气声
“你…你怎敢杀我?!”
公子嘉震惊,瞳孔逐渐涣散,不甘与遗憾隨著生机而逝去……
“私吞藏甲?”他扣动火銃扳机,又是一声枪响。
“且看这藏甲究竟属於谁!”项少龙挥刀劈开木箱,內里竟滚出刻著“嘉”字的青铜戈。
一幕僚脸色骤变,这些兵器是公子嘉半年前在代郡私铸,为的就是效仿李牧蓄养私兵。郭开忽然福至心灵,颤声喊道:“公子嘉私造兵器,意图谋反!”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项少龙调转枪口,连珠火銃的轰鸣震得树叶簌簌落下。勤王军前排的北军旧部轰然跪地,他们曾在李牧帐下听闻“秦军有弩车连射”,却从未想过有人能將如此利器藏在掌心。
……
……
咸阳宫的司天台传来更鼓声,贏乐望著铜镜里自己刻意点染的黑眼圈,捏皱了案头的密报。项少龙在桃林塞全歼公子嘉部的消息用硃砂圈了又圈,旁边批註著“火銃连杀三將”——这是韩夫人密信里从未提过的杀招。
“陛下,王翦求见。”宦官的通报声打断思绪,老將入殿时未著甲冑,只在腰间別了柄寻常青铜剑。
“项少龙已过函谷,”王翦將一卷舆图铺在地上,“其前锋距咸阳不过百里。”舆图上用红笔圈出三处隘口,贏乐的目光落在“灞上”標记上,那里曾是王翦二十年前驻军之处,如今却成了项少龙的必经之路。
“將军觉得该如何应对?”他故意將“將军”二字咬得极重,王翦的手指在“驪山”字样上顿住。老將忽然从怀中掏出个蜡丸,里面是项少龙兵营的布防图——標註者的笔跡,竟与韩夫人的密信如出一辙。
与此同时,项少龙的中军帐內瀰漫著药石气息。他拆开雅夫人最新密信,“贏乐知蛊”四字被涂改成“王翦有图”,末尾画著司天台的星象图——那是咸阳宫密道的另一个入口。
“將军,”副將压低声音,“那墨家工匠说,这种连珠火銃最多再射三次,簧片就会断裂。”项少龙摩挲著枪管上的纹路,陷入沉思。
他转头望向帐外,公子嘉的残部正在整编,那些北军旧部看著他腰间的箭囊,眼神已从敌意转为敬畏。
………
………
咸阳城外三十里,渭水被初阳染成熔铁般的赤红色。项少龙立於战车之上,黑色披风在燥热的晨风中猎猎作响。他身后是三国联军——赵军飞燕旗、楚军赤凤幡、魏国苍狼徽在沙尘中连成一片血色海洋。
“报!秦军阵中异动!“斥候嗓音嘶哑,“那些铜怪物...在列阵!“
项少龙眯眼远眺。地平线上,数十尊三米高的青铜机关兽正缓缓展开躯体,关节处喷出蒸汽白烟。最前排的机关兽突然集体仰头,喉间齿轮转动发出刺耳的金属嘶鸣。
“装神弄鬼。“项少龙冷笑,挥手间三百架投石机同时扬起,“让他们见识下真正的'战爭'!“
三千枚陶罐火雷被投石机拋向秦军左翼。这些看似粗陋的土罐在半空突然裂开,洒下漫天火油,紧接著火箭齐发——
“轰!“
渭水北岸瞬间化作火海,三十名秦军来不及分散就被气浪掀飞。但火焰中突然衝出五头机关兽,它们覆满铜鳞的背部“咔嗒“翻起钢板,竟將燃烧的油脂尽数抖落!
“换毒气弹!“项少龙怒吼。
第二轮投射的陶罐在半空炸出绿色毒烟,最前排的机关兽突然踉蹌——毒雾腐蚀了齿轮间的松脂润滑剂!
………
战鼓突然转为急骤的密点,如丧钟般捶打每人心臟。秦军黑底狼首战旗下,方阵如活物般裂开,三百名轻甲兵士上场,手持燧发枪,踩著同一节拍推进,鹿皮护腕蹭过枪管的沙沙声里,第一排枪口已喷出白烟。铅弹撕裂两名楚军盾牌手的胸甲,血在青铜圆盾上绽开时,后排机关兽的巨掌碾碎满地断箭,战鼓每响一声,便逼近三步。
那尊“伐天巨兽“伏低的脊背最先撞破硝烟,青铜鳞片在血光中泛起幽蓝,四爪刨起的碎石打在联军盾牌上叮噹作响。楚军百夫长刚要喝令放箭,却见那庞然大物突然人立而起,前肢的青铜护套轰然展开,原本下垂的伐木斧“咔嗒“弹出七道锯齿,在夕阳下连成三米长的弧形光刃,锯齿间还掛著未乾的褐色黏液——不知是多少人的血与脑浆凝结而成。
“放——“
喝令戛然而止。锯齿刃横扫的瞬间,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排头十二名弓手连人带弓被齐齐削断,上半身飞坠时,腰腹断口的血柱喷得比盾牌还高。更骇人的是锯刃触血的剎那,锯齿突然向內翻转,整把刃口竟化作高速旋转的钻头,將落地的尸体绞成肉泥,混著碎骨的血雾被甩向后方,前排盾牌手的青铜面甲上顿时糊满温热的黏浆,透过呼吸孔钻进鼻腔的,是混杂著铁锈味的肝腥味。
机关兽的喉管里传出齿轮摩擦的尖啸,竟与秦军战鼓的节奏严丝合缝。它前爪踏碎一名试图爬走的伤兵,钻头般的刃口突然刺入地面,带起的碎石如霰弹般扫过第二排楚军,几名士兵的眼球被石片直接撞出眼眶。更令人胆寒的是它背部的青铜舱盖缓缓打开,两名秦军锐士戴著兽首面具,站在液压升降台上举著喷火器,粘稠的火油顺著兽嘴状喷口滴落,在焦土上滋滋冒烟。
“后撤!后撤!“楚军指挥旗开始疯狂摇晃,但伐天巨兽的铁尾已如青铜柱般扫来,扫中一名旗手的瞬间,尾端的三稜锥突然弹出,將人钉在身后的拒马桩上,旗杆上的“楚“字大旗被血浸透,在夜风中沉甸甸地垂下,宛如一块正在凝固的血布。燧发枪手的第二轮齐射恰在此时轰鸣,铅弹穿透盾牌的闷响与机关兽的金属嘶吼交织,渭水北岸的暮色,已被染成浓得化不开的黑红。
……
大帐內,项少龙气欲吐血,为什么机关兽都出现了?!早知这么乱,攻什么咸阳吶,立即逃往海外猥琐发育才是王道。
抚过腰间鹿皮袋里的青铜虎符,此刻正被掌心的冷汗浸得发烫。
“来人!派八百死士!备…”
副將陈武率八百死士伏在土坡,后背的陶瓮隨著呼吸轻晃,鱼油混合硫磺的刺鼻气味钻进甲缝,与每个人喉间的铁腥味酿成苦胆般的滋味。他余光扫过身旁的老兵,那人左脸的刀疤从眼角划到下頜,正用断指的手蘸著血,在陶瓮上歪歪扭扭画著家乡的麦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