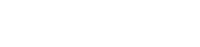咸阳宫暖阁內,炭火烧得正旺,贏乐捏密报,居然又跑了。密报末尾“项少龙携红阳公主东逃”的字跡旁,还洇著几滴暗红——不知是硃砂还是人血。
李斯抚著山羊鬍的手顿了顿,袖中玉佩轻响。他早料到项少龙的逃亡会成为绝佳藉口,却未想到贏乐竟如此急切。“我王初登大宝,正该以雷霆之威震慑六国。”他眼角余光扫过阶下低头的蒙恬,“不过...二十万大军调动需时,粮草...”
“粮草已备齐三月之量。”蒙恬突然开口,身著轻甲下的脊背挺得笔直,“函谷关驻军今早送来急报,韩军近日在边境增筑壁垒,显然心怀不轨。”
贏乐抬眼,与李斯对视。这个总在阴影里磨墨的男人,果然什么都算好了。他转向窗外,远处太庙的飞檐在暮色中如展翅的玄鸟,突然想起一句话:“所谓王者,不是看谁拳头硬,而是看谁能让天下人觉得拳头该硬。”
“明日辰时,祭天大典。”他抓起案上的秦王剑,剑鞘上的饕餮纹蹭过锦缎,“传寡人命:《討韩檄文》由廷尉亲自撰写,要让六国小儿闻之夜啼。”
………
太庙广场已跪满文武百官。青铜鼎中飘起的艾草烟裹著血腥气,十二名童男童女捧著牲畜肝臟,在祭坛前排成一列。贏乐踩著湿漉漉的石阶而上,玄色龙袍下摆扫过台阶上的血渍——那是昨夜宰杀的三牲之血,按周礼需在祭战前涂於祭坛四角。
“天佑大秦!”司祭官高举玉圭,声音穿透晨雾。贏乐接过酒樽,却未按规矩泼洒,而是反手將酒液浇在祭坛边缘的青铜柱上。酒液顺著柱身的蟠螭纹流下,在“受命於天”的铭文上积成细流,宛如泣血。
“韩国逆贼!”他突然掷樽於地,碎瓷声惊飞檐角宿鸟,“扣押寡人的左庶长,私通赵国公主,暗修兵器於阳翟!”他转身指向东方,九旒王冠上的玉珠簌簌作响,“今日起,寡人亲率王师伐韩,必取韩王首级,悬於函谷关!”
阶下群臣震恐,李斯的目光在贏乐腰间的剑柄上停留——那是秦王政留下的“定秦剑”,此刻被这个少年握在手中。他注意到蒙恬嘴角扬起的弧度,突然想起三年前在秦王宫,这个年轻人曾跪在嬴政脚下说:“愿为陛下手中刃,斩尽挡路者。”
“吾王万岁!”李斯率先叩首,声音里带著滚烫的虔诚。百官隨之伏拜,山呼声中,贏乐看见远处宫墙上掠过一道黑影——是白锐的暗卫。他摸了摸剑柄,那里藏著项少龙临走前留给他的羊皮卷,上面用楚文写著:“若敢负天下,我必夺你狗命!”
…………
隨著沉重的军號响起,呜呜呜!函谷关的烽燧燃起青焰。二十万秦军的呼吸声匯集成低沉的潮鸣。他按住腰间剑柄,龙鳞甲下的中衣已被冷汗浸透——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如此庞大的军阵,比电视里诸葛亮摆的“九宫八卦阵”大上百倍。
“列阵!”蒙恬的吼声如雷贯耳。
首先动起来的是重装步兵。八万士卒身著熟牛皮甲,手持两丈长的鈹矛,每十人一列,步调整齐得如同机械。当第一排战旗举起时,贏乐眼前骤然一暗——黑色的“秦”字战旗遮天蔽日,旗面上的猩红狼首图腾在风中扭曲,像要择人而噬。
贏乐踩著石阶跃上点將台,腰间秦王剑的玉璏磕在台沿,迸出火星。
“诸將听令!”他扯开喉间铁闸,声浪碾过前排持旗手,黑色“秦”字大旗轰然展开,猩红狼首在狂风中齜开利齿,“韩人占我宜阳铁山,窃我大秦文化,铸剑指我咽喉!今日观兵,非为演武——”袍角扫过將台边缘,他猛然抽出长剑,剑芒劈开沉沉暮色,“是要教天下知道,挡我东出者,唯有白骨铺路!”
台下甲冑骤响,如冰河开裂。贏乐踏前半步,剑尖直指南方:“二十年前,我父孝公饮恨河西时,韩人曾笑我『秦无锐士,甲不过皮,兵不过木』!”某排百夫长突然单膝砸地,鈹矛顿地声惊飞夜鸦,“今日且看!”他挥剑划过阵列,八万牛皮甲同时反光,“我大秦锐士的熟甲,可扛得住韩卒劲弩?!”
“扛得住!”第一列方阵轰然回应,声浪掀得战旗狂舞。
“再看这鈹矛!”贏乐剑指丈二长兵,“韩人铁剑虽利,可曾见过我大秦工匠铸的精铁矛头?!”第二排士卒齐举兵器,金属碰撞声如雷霆滚过函谷,“三日后兵发宜阳,我要你们用这矛头,挑了韩王的金冠!”
“挑金冠!”方阵中爆发出混著唾沫的嘶吼,有人用矛头敲击甲冑,节奏越来越急,如战鼓催征。贏乐忽然將剑鞘砸在將台石面,爆喝:“风!”
“风!”第一排战旗骤举,如黑海涌起巨浪。
“大风!”第二排士卒顿足,大地在甲靴下战慄。
“破宜阳!屠韩军!”贏乐长剑直指新郑方向,八万声音突然凝成尖啸,“风——!大风!!大风!!!”狼首战旗在夜空中翻涌如血,贏乐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全军的嘶吼共振,仿佛整个关中平原都在脚下沸腾,那些被韩人剋扣的铁料、被窃取的文化、被割占的城邑,都將在这声浪中碎成齏粉。
…………
“报——!”一名探马突然从关外奔来,“韩国上將军韩朋率十五万大军屯於宜阳,距此仅百里!“
帐內顿时譁然。李斯眉峰一挑,看向贏乐。少年却突然笑了,伸手按住蒙恬按在剑柄上的手:“將军可知,当年穆公伐郑时,如何应对敌军埋伏?”
蒙恬一愣,想起兵书里的记载:“先发制人,后发制於人。”
“正是。”贏乐解下腰间玉佩,拋给蒙恬,“蒙將军,率三千轻骑绕后,断其粮道。“他转身指向投石车阵列,“王上將军,命工匠在石弹裹上桐油,待夜风起时...”
………
一阵狂风突然捲起沙尘,贏乐看著自己挥动令旗的手,龙鳞甲在阳光下泛著冷光,突然想到白起教他练剑时说的话:“握剑要稳,但杀人要狠。”
“投石车,发!”他大吼一声,一千架投石机同时后仰,裹著桐油的石弹破空而去,在天际划出暗红的弧线。远处宜阳方向,韩军的营垒突然腾起火光,隱约传来惊呼声。李斯望著少年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总在阴影里读书的孩子,此刻竟像变了个人。
…………
戌时初刻,中军大帐內烛火摇曳。贏乐展开李斯派人送来的密信,瞳孔骤然收缩——信中写著:“黄四郎命人在粮草中掺沙,三日后必生譁变。”
帐外突然传来脚步声,他迅速將信塞进甲冑內衬。白锐掀帘而入,手中捧著一碗参汤:“我王劳累,先饮了这汤。”
“劳你掛心。”贏乐接过汤碗。
“听说王上要派蒙恬断后?”白锐语气轻缓,“会不会太年轻气盛,不如让...”
“你莫非信不过蒙將军?”贏乐突然抬眼,目光如剑,“还是说...觉得寡人调度有误?”
白锐心中一凛,这才注意到贏乐腰间的定秦剑已出鞘三寸,寒光映得他脸色发白。帐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天乾物燥,小心火烛——”
“不敢。”白锐后退半步,躬身时看见贏乐甲冑下露出的一角羊皮,眼神微变,“只是粮草之事...还需从长计议。”
“粮草?”贏乐放下汤碗,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廷尉方才送来军报,说三日后必有大雨,你觉得,这雨会不会衝散某些...沙粒?”
白锐浑身一震,终於明白李斯为何突然倒向贏乐。帐外风声骤起,远处传来投石车的轰鸣,他突然想起自己初见贏政时,那个孩子也是这样眼神清亮,却藏著深不见底的潭水。
“臣失察。”他再次叩首,额头触到帐中石板,“愿听我王差遣。”
贏乐看著白锐的背影,想起前世书中的一句话:“权力就像炭火,握得太紧会烫手,放得太松会熄灭。”他摸了摸藏在甲冑里的密信,突然笑了——不管敌人在哪里,都是谁,现在他是君王,君王怒,伏尸百万,且待著吧。
李斯抚著山羊鬍的手顿了顿,袖中玉佩轻响。他早料到项少龙的逃亡会成为绝佳藉口,却未想到贏乐竟如此急切。“我王初登大宝,正该以雷霆之威震慑六国。”他眼角余光扫过阶下低头的蒙恬,“不过...二十万大军调动需时,粮草...”
“粮草已备齐三月之量。”蒙恬突然开口,身著轻甲下的脊背挺得笔直,“函谷关驻军今早送来急报,韩军近日在边境增筑壁垒,显然心怀不轨。”
贏乐抬眼,与李斯对视。这个总在阴影里磨墨的男人,果然什么都算好了。他转向窗外,远处太庙的飞檐在暮色中如展翅的玄鸟,突然想起一句话:“所谓王者,不是看谁拳头硬,而是看谁能让天下人觉得拳头该硬。”
“明日辰时,祭天大典。”他抓起案上的秦王剑,剑鞘上的饕餮纹蹭过锦缎,“传寡人命:《討韩檄文》由廷尉亲自撰写,要让六国小儿闻之夜啼。”
………
太庙广场已跪满文武百官。青铜鼎中飘起的艾草烟裹著血腥气,十二名童男童女捧著牲畜肝臟,在祭坛前排成一列。贏乐踩著湿漉漉的石阶而上,玄色龙袍下摆扫过台阶上的血渍——那是昨夜宰杀的三牲之血,按周礼需在祭战前涂於祭坛四角。
“天佑大秦!”司祭官高举玉圭,声音穿透晨雾。贏乐接过酒樽,却未按规矩泼洒,而是反手將酒液浇在祭坛边缘的青铜柱上。酒液顺著柱身的蟠螭纹流下,在“受命於天”的铭文上积成细流,宛如泣血。
“韩国逆贼!”他突然掷樽於地,碎瓷声惊飞檐角宿鸟,“扣押寡人的左庶长,私通赵国公主,暗修兵器於阳翟!”他转身指向东方,九旒王冠上的玉珠簌簌作响,“今日起,寡人亲率王师伐韩,必取韩王首级,悬於函谷关!”
阶下群臣震恐,李斯的目光在贏乐腰间的剑柄上停留——那是秦王政留下的“定秦剑”,此刻被这个少年握在手中。他注意到蒙恬嘴角扬起的弧度,突然想起三年前在秦王宫,这个年轻人曾跪在嬴政脚下说:“愿为陛下手中刃,斩尽挡路者。”
“吾王万岁!”李斯率先叩首,声音里带著滚烫的虔诚。百官隨之伏拜,山呼声中,贏乐看见远处宫墙上掠过一道黑影——是白锐的暗卫。他摸了摸剑柄,那里藏著项少龙临走前留给他的羊皮卷,上面用楚文写著:“若敢负天下,我必夺你狗命!”
…………
隨著沉重的军號响起,呜呜呜!函谷关的烽燧燃起青焰。二十万秦军的呼吸声匯集成低沉的潮鸣。他按住腰间剑柄,龙鳞甲下的中衣已被冷汗浸透——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如此庞大的军阵,比电视里诸葛亮摆的“九宫八卦阵”大上百倍。
“列阵!”蒙恬的吼声如雷贯耳。
首先动起来的是重装步兵。八万士卒身著熟牛皮甲,手持两丈长的鈹矛,每十人一列,步调整齐得如同机械。当第一排战旗举起时,贏乐眼前骤然一暗——黑色的“秦”字战旗遮天蔽日,旗面上的猩红狼首图腾在风中扭曲,像要择人而噬。
贏乐踩著石阶跃上点將台,腰间秦王剑的玉璏磕在台沿,迸出火星。
“诸將听令!”他扯开喉间铁闸,声浪碾过前排持旗手,黑色“秦”字大旗轰然展开,猩红狼首在狂风中齜开利齿,“韩人占我宜阳铁山,窃我大秦文化,铸剑指我咽喉!今日观兵,非为演武——”袍角扫过將台边缘,他猛然抽出长剑,剑芒劈开沉沉暮色,“是要教天下知道,挡我东出者,唯有白骨铺路!”
台下甲冑骤响,如冰河开裂。贏乐踏前半步,剑尖直指南方:“二十年前,我父孝公饮恨河西时,韩人曾笑我『秦无锐士,甲不过皮,兵不过木』!”某排百夫长突然单膝砸地,鈹矛顿地声惊飞夜鸦,“今日且看!”他挥剑划过阵列,八万牛皮甲同时反光,“我大秦锐士的熟甲,可扛得住韩卒劲弩?!”
“扛得住!”第一列方阵轰然回应,声浪掀得战旗狂舞。
“再看这鈹矛!”贏乐剑指丈二长兵,“韩人铁剑虽利,可曾见过我大秦工匠铸的精铁矛头?!”第二排士卒齐举兵器,金属碰撞声如雷霆滚过函谷,“三日后兵发宜阳,我要你们用这矛头,挑了韩王的金冠!”
“挑金冠!”方阵中爆发出混著唾沫的嘶吼,有人用矛头敲击甲冑,节奏越来越急,如战鼓催征。贏乐忽然將剑鞘砸在將台石面,爆喝:“风!”
“风!”第一排战旗骤举,如黑海涌起巨浪。
“大风!”第二排士卒顿足,大地在甲靴下战慄。
“破宜阳!屠韩军!”贏乐长剑直指新郑方向,八万声音突然凝成尖啸,“风——!大风!!大风!!!”狼首战旗在夜空中翻涌如血,贏乐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全军的嘶吼共振,仿佛整个关中平原都在脚下沸腾,那些被韩人剋扣的铁料、被窃取的文化、被割占的城邑,都將在这声浪中碎成齏粉。
…………
“报——!”一名探马突然从关外奔来,“韩国上將军韩朋率十五万大军屯於宜阳,距此仅百里!“
帐內顿时譁然。李斯眉峰一挑,看向贏乐。少年却突然笑了,伸手按住蒙恬按在剑柄上的手:“將军可知,当年穆公伐郑时,如何应对敌军埋伏?”
蒙恬一愣,想起兵书里的记载:“先发制人,后发制於人。”
“正是。”贏乐解下腰间玉佩,拋给蒙恬,“蒙將军,率三千轻骑绕后,断其粮道。“他转身指向投石车阵列,“王上將军,命工匠在石弹裹上桐油,待夜风起时...”
………
一阵狂风突然捲起沙尘,贏乐看著自己挥动令旗的手,龙鳞甲在阳光下泛著冷光,突然想到白起教他练剑时说的话:“握剑要稳,但杀人要狠。”
“投石车,发!”他大吼一声,一千架投石机同时后仰,裹著桐油的石弹破空而去,在天际划出暗红的弧线。远处宜阳方向,韩军的营垒突然腾起火光,隱约传来惊呼声。李斯望著少年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总在阴影里读书的孩子,此刻竟像变了个人。
…………
戌时初刻,中军大帐內烛火摇曳。贏乐展开李斯派人送来的密信,瞳孔骤然收缩——信中写著:“黄四郎命人在粮草中掺沙,三日后必生譁变。”
帐外突然传来脚步声,他迅速將信塞进甲冑內衬。白锐掀帘而入,手中捧著一碗参汤:“我王劳累,先饮了这汤。”
“劳你掛心。”贏乐接过汤碗。
“听说王上要派蒙恬断后?”白锐语气轻缓,“会不会太年轻气盛,不如让...”
“你莫非信不过蒙將军?”贏乐突然抬眼,目光如剑,“还是说...觉得寡人调度有误?”
白锐心中一凛,这才注意到贏乐腰间的定秦剑已出鞘三寸,寒光映得他脸色发白。帐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天乾物燥,小心火烛——”
“不敢。”白锐后退半步,躬身时看见贏乐甲冑下露出的一角羊皮,眼神微变,“只是粮草之事...还需从长计议。”
“粮草?”贏乐放下汤碗,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廷尉方才送来军报,说三日后必有大雨,你觉得,这雨会不会衝散某些...沙粒?”
白锐浑身一震,终於明白李斯为何突然倒向贏乐。帐外风声骤起,远处传来投石车的轰鸣,他突然想起自己初见贏政时,那个孩子也是这样眼神清亮,却藏著深不见底的潭水。
“臣失察。”他再次叩首,额头触到帐中石板,“愿听我王差遣。”
贏乐看著白锐的背影,想起前世书中的一句话:“权力就像炭火,握得太紧会烫手,放得太松会熄灭。”他摸了摸藏在甲冑里的密信,突然笑了——不管敌人在哪里,都是谁,现在他是君王,君王怒,伏尸百万,且待著吧。